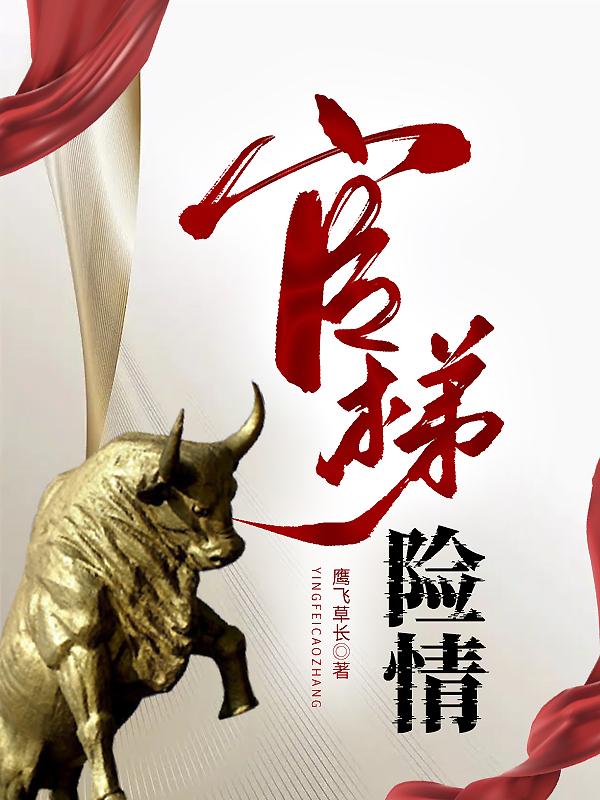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高阳的历史都有哪些 > 李慈铭褚成溥(第12页)
李慈铭褚成溥(第12页)
黄彭年之父名辅辰,字琴坞,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醴陵,官至陕西凤邠道,殁于任内,入祀名宦祠。黄辅辰道光十五年成进士后,以部员用,由吏部主事累迁至郎中,有“硬黄”之称。《十朝诗乘》载:
贵筑黄琴坞观察,道光中官吏部,与同僚遍稽旧案,分别存销。存者分类入簿,又手抄小册,随检即得,吏不能欺。且屡与堂上官抗争,因有“硬黄”之目。自纪诗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赢得人呼作硬黄。”
黄彭年字子寿,饶有父风。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先随父在籍办团练,后入骆秉章幕;同治初又主关中书院;又为其同年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志莲池书院。虽为告假的编修,但颇负时望;光绪八年特旨授为湖北襄郧荆道,欣然奉诏,以此为他的儿女亲家王湘绮所讥。
其实,黄彭年是有用世之志的。入仕应该有个迁转进身之阶,他不能在同年早就当到督抚,还回翰林院去当编修,等到“开坊”转侍讲、侍读学士,升京堂,再补内阁学士,方能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得有发抒抱负的机会,但那一来非二十年不为功,因而屈就道员,等一擢监司,便得展长才。
果然,黄彭年的路子是走对了,不久即升湖北臬司,《清史稿》说他此时“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余结京控案四十余起,平反大狱十数”。
但在湖北不能久于任,这也是可想而知的。臬司如此出色,足见巡抚尸位,自然排之而后快。黄彭年一调陕西,署理藩司,旋于光绪十一年调补江苏藩司。《清史稿》本传:
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余补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
光绪十四年十月,疆吏有一大调动,皖抚陈彝内召,以桂抚沈秉成调补;江苏崧骏,山西刚毅,浙江卫荣光三巡抚大扳位,即崧骏移浙,卫荣光移晋,而刚毅移苏。崧骏交卸后,由黄彭年署理江苏巡抚;刚毅卸任后,却迟迟不赴新任,原因甚多。其时江南大旱,方议赈济;而大婚及颐和园工程,皆需巨款;乃流民数千,强占荒田,江苏的情形极糟。刚毅虽称能员,去了亦未必有办法;而最主要的是,以刚毅的个性,与强项的黄彭年永不能相合;所以一直在京中观望。枢府亦以为此时的江苏,既由黄彭年主政,不宜掣肘,所以亦并不催刚毅赴任。
到了这年七月间,张之洞调湖广。此公居官,喜欢揽权用威是有名的,初到广东时,即与粤抚倪文蔚大起龃龉。胡思敬《国闻备乘》记云: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游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藐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卸吏事不问也。”
百川惧,归检会典,仓卒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督署,而巡抚成虚设矣。
此记中的巡抚,即为倪文蔚;但藩司非游百川,而为游智开(见《一士类稿》)。及倪文蔚不堪张之洞的压制,光绪十二年四月活动入觐,旋调河南;粤抚初由湖北巡抚谭钧培调任,亦深以为苦,至冬天云南巡抚出缺,谭钧培宁愿就滇,于是广东巡抚虽为好缺,竟无人逐鹿,副都御史吴大澂,乃得脱颖而出。
胡钧所作《张之洞年谱》“后序”云:
公督粤时,内简吴大澂为粤抚。电致吴云:“吾其为官文恭矣!”嗟乎,欲为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鸣求友,抑可伤已(原注:吴承倪文蔚之后,倪与公大龃龉)。
胡钧此论,为护师门,颠倒黑白。致吴大澂一电,是有意要改变一个公认的看法,即张之洞过于揽权。究其实际,他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官文,亦从未期望任何巡抚为胡林翼。
现在要谈樊增祥函中的所谓“高密”了。高密既指高密侯邓禹,而又非“仲华”,则所隐指之人,必姓邓,或名中有一禹字。细看当时缙绅,实指邓华熙。
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举人,光绪十五年由云南臬司于六月初调升湖北藩司。未几,张之洞由粤移鄂,见于上谕。邓华熙深知张之洞难侍候,复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张之洞以其为科目前辈而稍加礼遇,所以“自危”,求援孙毓汶。其弟不知何名,但孙毓汶任考官之时不多,或不难索解。
孙毓汶于咸丰六年,与翁同龢同膺鼎甲后,以为恭王所恶,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编修一主四川乡试;既未放过广东考官,亦未与北闱乡试,则邓华熙之弟,当非孙毓汶的乡举门生。
自光绪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枢,孙毓汶入政府后,于光绪十二年以工部侍郎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以“正大光明”排列,位居“光”字。吏部尚书蒙古锡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寿阳祁世长,既为后辈,又无衡文之名,且为人老实。孙毓汶之下为户部侍郎满洲嵩申,更无足与数,所以此科完全由孙毓汶一手主持。
查题名录,光绪十二年会试,三甲第十七名邓士芬,广东英德人,殆即其人。顺德属广州府,英德则在韶州,当系远宗,或者“认本家”,此在科举时代亦为常有之事。
所谓“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即是硬拉关系。如邓华熙为邓士芬胞兄或近支从兄,则以通家子弟礼见孙,可以公然磕头,不必“夤缘”。邓为咸丰元年举人,孙为咸丰六年进士,年齿及乡榜,邓皆高于孙,而“以弟子礼见济宁”,且“绝爱怜之”,此是樊增祥下笔轻薄;但亦足见邓华熙畏张之洞,不惜卑躬屈节,务求去鄂。而苏鄂两藩司,亦即黄彭年与邓华熙对调,则别有缘故在。说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抚的一种手法。
军机对张之洞头痛,对黄彭年亦未必不伤脑筋。江苏京官而在原籍有田产者,对于黄彭年动辄想减租,帮佃农讲话的作风,颇有戒心。“星下”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误字,以情理而论,除非江督曾国荃致书军机,言“醴陵尽闹脾气”,才会考虑调动黄彭年,而借口“鄂藩需才”,自是不通的说法;鄂藩需才,莫非苏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不会不干预湖北的钱粮、民政,而黄彭年亦绝不会唯命是从。互不相下就必然演变成互相攻讦;在樊增祥看,这是“同室操戈”,徒使亲痛仇快,因与黄彭年之子国瑾(字再同)相商,谋调和之计。
以下谈京中大老近况,接叙得自许景澄的消息谓:
竹筼昨日谈及,大圣近来于函丈亦不甚为难。常熟虽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不肯显然树敌。户部自子开物故,实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则广东报销,无复他虑矣。
竹筼又云,凡兵部有所驳斥,函丈初疑洨长为之,实则不然。兵部现由香山当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笃,(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复多次)。传说身如枯木,山东林令来声言无碍,人初以为妄,近日居然大愈,禀赋可谓极厚,亦国家之福也。
竹筼即许景澄,出使德国因丁忧回国,此时方起复在京,任翰林院侍讲,“大圣”即孙毓汶。“洨”指先恭慎公,《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选除洨长。”洨者,洨县之长;切许姓。先恭慎其时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在枢桓之时为多,所以兵部“由香山当家”。庄练兄谓“香山”指兵部右侍郎白桓,以香山切白姓;良是。按:白桓字建侯,直隶通州人,同治二年进士,用为部员,分吏部,积资升至文选司掌印郎中,掌文官除授,为京官中有名的好缺;李慈铭称他“清强有声,吏不敢为私”。光绪六年升内阁侍读学士。其任兵部右侍郎在十五年二月;所谓“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因吏、兵两部,文武不同之故。
“邸病”指醇王之病。黄秋岳谓函中以醇王病愈“亦国家之福”,因“醇王为德宗之父,故曰国家之福”,此一解释,未免浅露。其实乃指翁同龢而言,翁为帝师,德宗信任方专;但有醇王在,多少可以裁抑翁同龢。樊增祥的意思是,如醇王不起,翁将益发难制,故醇王病愈为国家之福。
按:醇王因“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平生雄心壮志,都成虚话。清议与神明交责,衾影自惭,抑郁寡欢,因致沉疴。自光绪十三年冬天起,即长在休养之中。至光绪十六年七月,复又中风。据翁同龢是年日记:
七月初九:是日上回宫,行礼毕后出后门诣醇邸府,皇太后辰刻前往也。归小憩,入署遇孙、徐二君。午刻问醇邸疾,晤福相于左近公所,见昨日脉案,始悉昨午正抽风,口眼歪斜,遗溺,神识不清,视物不见等症。酉刻子刻两方云稍愈,痰得下,夜进糕干两块,脉见代象,危险云云,药则人参黄芪而已。因诣府亲问,云今日方未下,似稍转机。戈什爱班等在内,不便往谈,遂归。日暮着人问,则云进粥半碗,神渐清(昨厥五刻始苏,雷雨时适渐清,其门上言如是)。上申刻还宫,太后中正还官,明日未定再诣与否。
七月初十:辰初上至书房,语甚是,退时早。诣醇邸问疾,见昨今案方,方大致同,案称今日辰刻得大解,脉代象退,惟目视不明,手仍掣动,饮人乳数口,进粥半碗。
七月十一日:两次遣人问醇邸病,昨日大便二次,今日案云自酉至卯大便四次,目视物仍不清,药用参芪等补中益气。自余观之,恐元阳已陷矣。
七月十二日:上诣建福宫行礼后即诣醇邸看视,皇太后于辰刻前往(申正回)。
奇怪的是,自此以后,翁记中并无此君臣二人视疾的记载,直至七月廿八日,始有“问醇邸疾仍如前”一语。殆慈禧不喜人与醇王过亲近之故。至八月初二日又有记:
八月初二日:寅正二刻引见吏部,内阁堂未到齐,即往醇王府看视。到朝房坐良久,退诣邸,闻云昨日已正厥四刻,夜亥正复厥四刻,胸胀神不清,小水数,大便不下,医云攻补两难。时上已到,太后尚未到也。
出城拜客,过厂,入署事繁(复奏顺直赈务,徐小需云原折专指顺天,不以直隶阑入,因改请福相酌之)。未初归寓,检书,周生霖来辞行,后日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