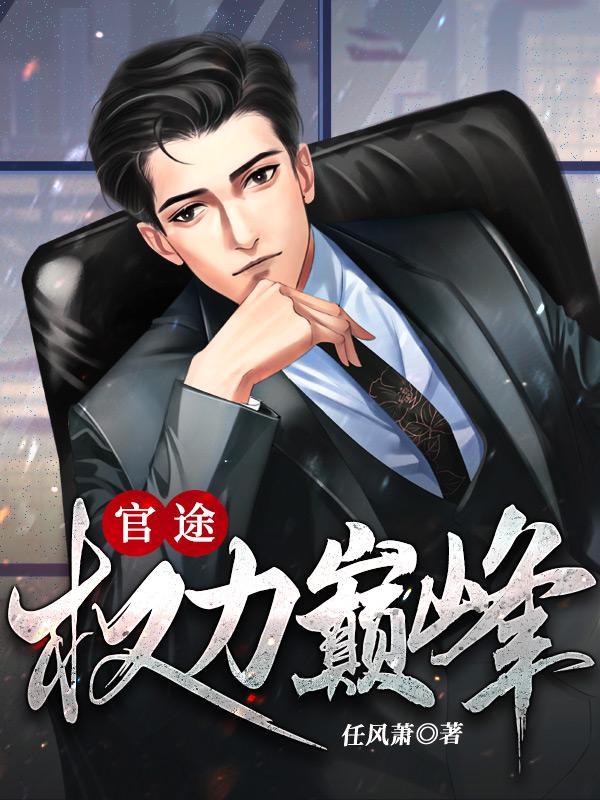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为了一个亿养了一条龙全文阅读 > 3040(第8页)
3040(第8页)
吕午指了指远处的沙丘,“我把他藏那边了。”
芒昼执缰掉头,右手持刀,稳稳把董天心圈在怀里,“抓稳!”
话音未落,纵马杀了出去,董天心紧急伏身,双手死死抓住马鬃,这一次坐得高了,视线也清晰了不少。
两拨人正在激烈厮杀,一队人身着革甲,骑着高头大马,样貌凶恶,表情狰狞,除了被芒昼砍翻的三四匹马,还有五六匹,另一队人只有四个人,没有马,举着刀,穿着藤甲布衣草鞋,全是拼命的招式。
两边都是边喊边打,革甲一队嗓门巨大,喊得词叽里呱啦呜哩哇啦,完全听不懂,藤甲一队人不多,声势可不小:“匈奴蛮夷,犯我边境者死!”。
芒昼没有丝毫犹豫杀向了革甲一队,有了马,芒昼如虎添翼,对战那些匈奴兵如同切瓜剁菜一般,落花流水,一刀一个,眨眼间,只剩了一个残兵,吓得脸色发绿,纵马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劫后余生的四名藤甲兵傻了。
但见那黄天沙海之中,男子白衣黑马,手持血刃,仰头望着遥远的天际线,身颀如山,发丝镀金,如神祇临世。
突然,白衣男子看了过来,眸中残留的杀意翻涌如浪。四名藤甲兵如临大敌,同时握紧了手里的刀。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姑娘慢慢从马背上爬起来,软软靠近了男子怀中,长吁一口气,顶天立地的“神祇”双眼可见的一个激灵,翻身下马,手还勉强抓着缰绳,身体却躲得老远。
藤甲兵众揉了揉眼睛:“……”
董天心有些疑惑地瞥了眼芒昼,看向四名藤甲兵,四个人长得挺有特色,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瞪着圆溜溜的八只眼,张着嘴,颇有喜剧色彩。
董天心笑着招了招手道:“你好,请问这是哪年哪月哪地儿啊?”
四个藤甲兵愣住了几秒,不约而同露出姨母笑:“这是西境,黄沙堡。”
黄沙堡,名字里有个堡,但实际上,是一座小小的边陲小塞,南高北低,石块和土泥混合垒砌的城墙,缝隙里还夹杂着芨芨草、芦苇和红柳,城墙差不多两人高,堡门不大,只能并排走两匹马。
守堡戍卒看到董天心四人十分警惕,四名藤甲兵上前解释了几句,守堡卒便乐呵呵让行。
董天心大为惊讶,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起码要有个路引,或者被盘问几番才行,当即对这四名藤甲兵肃然起敬,想必身份不同凡响。
“哈哈哈,我们不是戍边卒,是黄沙置的邮卒,大家都唤我们‘卒同’,就是‘送信的’,几位恩公若是觉得麻烦,叫我们‘喂’也行。”矮个子藤甲兵笑道。
当然,不能真的叫人家“喂”(太不礼貌了吧啊喂)。吕午充分发挥了厚脸皮的交际天赋,几番套近乎,得到了一手信息。
负责带路的矮个子叫皮皮荣,是个木匠;个子最高皮肤黝黑的叫阿昌,当过两年兵,是黄沙堡里数一数二的刀法高手;面黄肌瘦的瘦子叫二南;胖乎乎的石九以前做过“养卒(负责做饭和后勤工作的兵种)”,现在是“黄沙置”的厨子。
所谓“置”,就是传递文书的中转驿站。黄沙置是官置,原本只传递官方文书,但这几年匈奴进犯越来越频繁,方圆百里的置都维持不下去,只剩了黄沙堡一处,责任重大,也开始传递民信,官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黄沙堡只有一条主街,一眼就能望到头,戍边兵卒的营房和驻塞百姓的草房沿街而建,再逐渐向外扩张,小小的房顶一个挨着一个,好像积木拼搭,门前都挂着门牌,还有分区编号,例如“卯兔丁巷四号”、“辰龙甲巷十六号”等等。
路上随处可见扛着锄头的兵卒,挎着菜篮子的百姓,见面都热络打招呼,相处很融洽的样子,皮皮荣他们人缘不错,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碰到了好几拨熟人。
扛着粟米的大娘:“啥时候去悬泉置送信啊?顺便带两坛悬泉酒回来呗。”
皮皮荣:“后天就去,酒肯定带回来。”
急匆匆的守谷卒:“我妹妹生了吗?男孩还是女孩?”
阿昌:“生了,女孩,你当舅舅了。”
十来岁的小兵卒:“我阿娘回信了吗?”
二南:“还没,改天我问问。”
颤颤巍巍的老人:“这封信一定要送给我阿弟。”
石九:“行嘞!徐老爹您放心。”
更多人的则是好奇地盯着芒昼——呃,芒昼牵着的马。
这匹马是芒昼从匈奴兵那抢来的,身材高大,毛色黑亮,一看就非凡品,可惜,现在只能苦哈哈驮着虚弱的左柏。
左柏自醒来之后就一直在嘀嘀咕咕什么“相对论时间穿梭宇宙黑洞”之类的理论,快把自己绕进去了,加上受惊过度和晕马,吐了一路,脸都绿了。
顶着好奇的视线,众人穿过主街,饶进小巷,很快就看到了“黄沙置”,一圈土坯墙,墙角竖着几丛干草,四间夯土房,一座马厩(居然还有马厩),一个厨房(露天的),一个柴房。
众人带回来的战利品(三大包马肉,四套皮甲,两柄弯刀,一匹活战马)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
“老朴,我们回来啦!”皮皮荣前脚进门后脚大喊,“小凑,快来瞧瞧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率先冲了出来,衣袖和裤角卷了好几层,草鞋有点大,差点绊一跤,看到董天心四人,愣住,噌一下钻了回去,又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提溜了出来。
老汉也有些惊讶,飞快看了一眼石九,“这几位是?”
皮皮荣迫不及待将今天他们送信回黄沙堡,不料途遭匈奴兵偷袭,命悬一线之际,天降神兵(主要指芒昼)得救,斩杀匈奴兵四人,得了一大堆战利品等等事迹,添油加醋说了一遍,吐沫星子都快喷出彩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