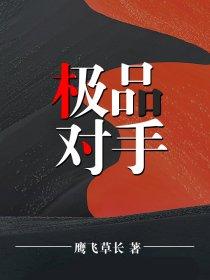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被迫营业linnay > 160180(第8页)
160180(第8页)
各行各业都有人渣。面对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不少“大佬”利用双方悬殊的社会地位、行业大佬的魅力加持,做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为了避免瓜田李下,如果有必要单独联系学生,胡驰从来都是通过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联系。
身为家长的杨陶璐妈妈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比女儿还要受宠若惊,恨不得立刻就让胡驰介绍同声传译圈里的人脉,让女儿跟着去学习。
杨陶璐妈妈根本不认识胡驰,但听说他40岁不到就翻译了好几本长篇科幻小说,更有三中请他做评委的行为背书。这让杨妈妈幻想起来:二十年后,孩子会跟着哪个国家领导人出访呢?
杨陶璐是走读生,平时在学校上晚自习,周末难得回家吃饭。孩子到了家,《新闻播报》在杨家的电视机上再也看不见了,80%的时间都固定在英文频道,哪怕杨爸爸杨妈妈一个词都听不懂。
反倒弄得杨陶璐心理压力非常大,甚至对翻译产生了逆反心理。好在高老师没有继续给她压力,让她顺着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去涉猎。
除了社会实践职业体验,高一下学期最重要的集体活动是合唱节。
就像运动会一样,三中的合唱节同样不走寻常路。与其说这是合唱节,不如说是三中为同学们举行的文艺汇演,或者叫艺术节。
三个年级分开举行,各班抽签决定合唱节目的顺序。合唱表演期间,还会穿插着一些个人表演、小团队表演项目。这些节目的报名全凭自愿。
不少同学即使耽误学习也愿意报名参演,是因为三中会在艺术节期间请来一些重量级嘉宾。
去年,三中请来的嘉宾中,包括一名在全国范围内都小有名气的舞蹈家。
观看了几位舞蹈特长生的表演,舞蹈家挑中了其中两人,想要吸纳进自己的舞团。
如果说成绩优秀的文化生可以通过学科竞赛等渠道,获得大学保送降分录取的资格,那么,三中的文艺汇演节,就是艺术特长生们获得保送的机会。只不过,保送单位可能不是大学,而是歌舞团、乐队等演出团体。
当然,有的同学虽然是艺术特长生,但特长只是他们为了升学而走的捷径罢了,他们本身对艺术专业并没有浓厚的兴趣,即使受到了专业人士的青睐,也有可能直接拒专业人士于门外。
拿10班的小提琴艺术特长生葛希瑶来说,且不提她的水平有没有一星半点的可能性被专业人士看上,即使葛希瑶被交响乐团邀请去当首席琴师,想到这辈子都要天天和小提琴打交道,那还不如从来没学过小提琴呢!
原则上说,除了合唱节目,每班最少单独再报一个表演节目。除此之外,还会多出六至七个节目的空闲时间,按照惯例,一般由多个班级合作排练节目,填充这些空缺。
这是孩子们的节日,高松然不想多加干涉。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办,他一个连五线谱都认不全的英语老师,还是少掺合这些为妙。
于是,他将10班的一切排练、报名工作,全权交给了宣传委员郑子叶,以及音乐课代表王笛负责。
第166章在任何一位高中老师看来,王笛都是一名“问题学生”
能在特长生云集的10班成为音乐课代表,王笛自然有些本事。
都说名字寄托了父母对孩子的美好愿望,话多的陈默属于令父母的愿望完全落空的孩子,而王笛,却正好相反——她是个学吹笛子的音乐特长生。
在任何一位高中老师看来,王笛都是一名“问题学生”。
开学第一天,前班主任黄巍就在教室公然训斥过王笛:“才16岁,搞什么纹身?跟小太妹似的!”
王笛在左右两边胳膊上各纹了一行字。右胳膊上,“永不止步”,洋溢着既中二又充满热情的青春气息。
左胳膊上同样的字体,却是七个字,“莫为乱花迷了眼”。
听起来像是由白居易的诗歌“乱花渐欲迷人眼”改编的,却改编成了一番大白话,逼格不高。
王笛对这两片纹身的态度也不尽然相同。这两片纹身的位置几乎镜像对称,但她似乎对于“永不止步”四个字感到骄傲,甚至还主动撸起右边的袖子,向身边朋友展示。
左边则不太一样。只要王笛穿了长袖衣服,左边的袖子永远服服贴贴地遮盖住胳膊,还有胳膊上的纹身。只有在她穿短袖时,同学们才能看得见这七个字。
每每有人问及这七个字背后的故事,王笛要么打哈哈糊弄过去,要么干脆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如黄老师这般的老派教师,自然看不惯王笛的纹身。更何况,年级组长邵老师、德育处的老师们,只要看到王笛,都会萌生出要找老黄聊聊天的冲动,让他管管班上的学生。
高中生纹身,成何体统?
但老黄也很冤枉——不是他不想管,是根本管不住!
王笛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平时和母亲一起生活。
开学第三天,受到领导狂轰滥炸的黄老师,无奈地和王笛妈妈通了个电话。
接通电话一分钟后,老黄就凭借他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意识到,王笛这个学生,很难管得住。
可以这么说,王笛是个个性叛逆的女孩,她的妈妈叛逆起来,比孩子只强不弱。王笛妈妈同样个性张扬。
别的家长因为孩子的表现而被班主任找来谈话,多半会先诚惶诚恐地向班主任道歉,再承诺一定监督孩子的行为。但王妈妈一开口就告诉老黄:“王笛,我管不动。”
车祸后,黄老师的身体稍稍恢复,高松然去医院看过他,顺便聊了聊10班的近况。
班里有好几个让黄老师在病榻上都不免担心的孩子,王笛是其中一个。
想起和王笛妈妈的通话,尽管已经过去了半年多,老黄依然怨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