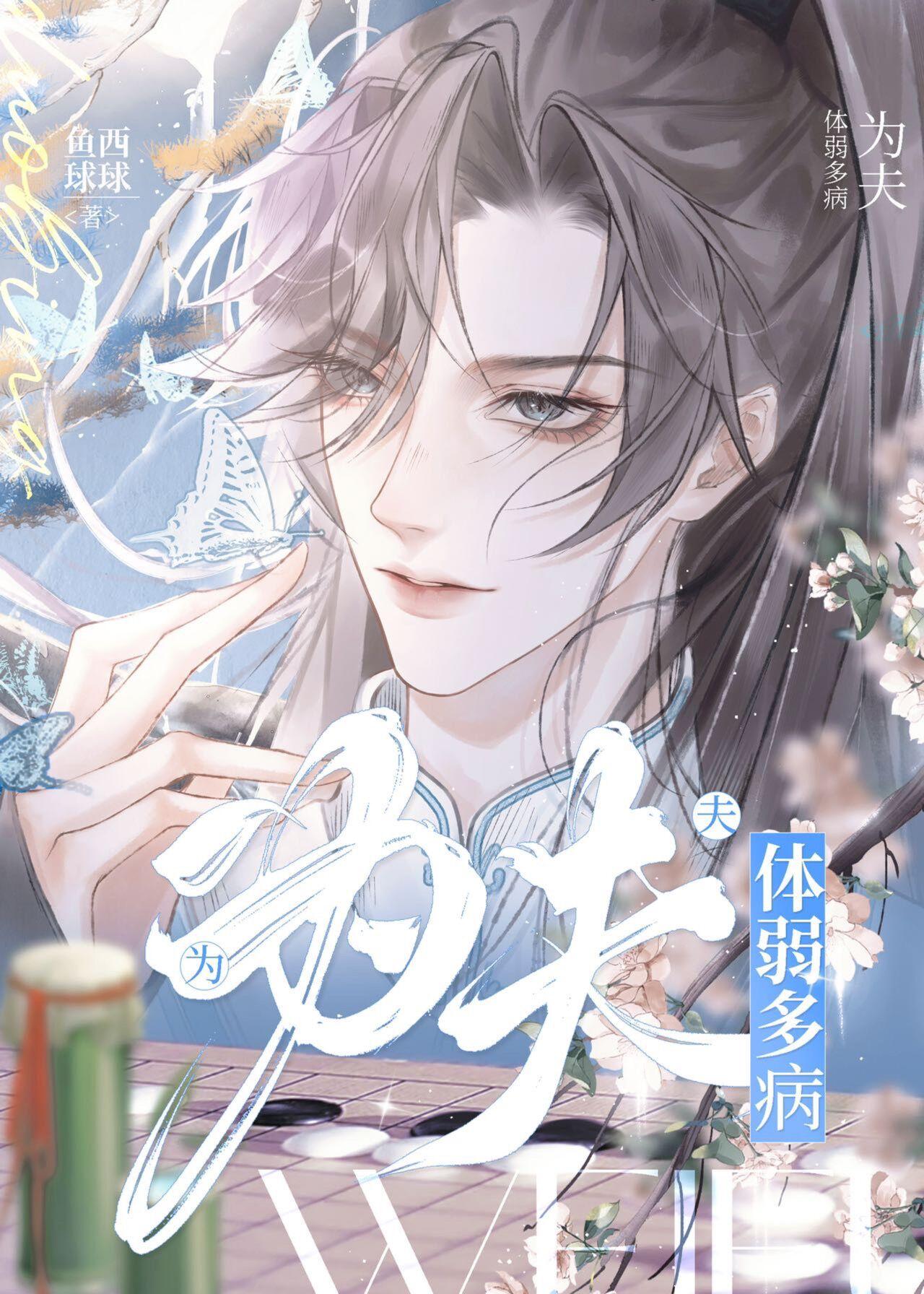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宇宙t恤 > 第22章 国际物理学大会上的灾难演讲(第2页)
第22章 国际物理学大会上的灾难演讲(第2页)
李默的演讲才进行到一半,但已经没有继续的空间了。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各种批判的目光,只有陈教授和林小雨给他鼓励的眼神。
问答环节变成了一场猛烈的攻击。每个问题都像一把利剑,直指理论的薄弱环节:缺乏实验验证、概念定义模糊、与主流理论冲突。
一位知名物理学家直接质问:"李博士,你的理论听起来更像是哲学或神秘主义,而非物理学。你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就在李默准备回答时,林小雨突然举手:"如果允许,我想提供一个哲学视角。"
主持人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林小雨站起来,声音平静但有力:"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突破最初都被视为'神秘主义'。量子力学刚提出时遭遇的质疑并不比李博士的理论少。从哲学角度看,李默博士的理论实际上是在尝试解决量子力学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观察者与被观察系统的关系。他的方法可能非常前沿,但绝非毫无根据。"
会场安静了几秒钟,林小雨的发言似乎让一些人开始思考。但很快,批评声又起来了。
"这正是问题所在,"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说,"物理学和哲学是不同的学科。物理学需要可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哲学思辨。"
会议的剩余时间变成了一场持久战。李默尽力应对每一个问题,但明显处于劣势。当讨论终于结束时,大部分与会者已经失去了兴趣,纷纷离场准备参加下一个议题。
只有几位年轻研究者留下来,似乎对李默的理论有一些好奇,向他询问更多细节。一位来自欧洲的量子计算研究员对他说:"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你的框架,但你关于量子信息处理的一些想法很有启发性。"
走出会场,李默感到精疲力竭。"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他对陈教授和林小雨说,"我完全失败了。"
"不,你没有,"陈教授坚定地说,"你勇敢地站在那里,面对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们,捍卫自己的理论。这已经是一种胜利。"
"而且,"林小雨补充道,"至少有几个人对你的想法表示了兴趣。科学革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于少数人的开放思考。"
李默微微点头,但内心依然沉重。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近他们。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性,穿着休闲西装。
"李博士?"陌生人用英语问道,"我是大卫·科恩,《科学前沿》杂志的编辑。你的演讲很有意思——尽管充满争议。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简短的采访?我们杂志下个月有一个关于'科学边界'的专题。"
李默惊讶地看着科恩,然后看向陈教授和林小雨。陈教授微微点头,而林小雨则轻声说:"这可能是一个传播你理论的机会。"
"好的,"李默对科恩说,"我很乐意接受采访。"
当晚,在酒店房间里,李默回顾着这场灾难性的演讲。他打开社交媒体,发现已经有人发布了他演讲的片段,配上了嘲讽的评论:"看看这位中国物理学家如何用'意识场'颠覆物理学——或者说是回到中世纪?"
林小雨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屏幕:"这些反应是意料之中的。但记住,科学史上充满了类似的故事。今天的嘲笑可能成为明天的教科书案例。"
李默苦笑着关上电脑:"问题是,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撑到'明天'。这次演讲后,我在学术界的名誉可能已经彻底毁了。"
陈教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三杯茶:"别那么悲观,李博士。科学的魅力之一就是,它最终只看重真相,而不是舆论。如果你的理论确实更接近真相,那么它终将被接受——无论过程多么艰难。"
李默接过茶杯,望向窗外的新加坡夜景:"关键是如何证明它。我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需要一个可以公开验证的实验方案。"
"而且你需要更谨慎地表达,"林小雨建议道,"也许可以先从量子信息处理的应用方面切入,那是最容易获得认可的部分。"
陈教授点点头:"明智的建议。每个革命性理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李默沉思片刻,突然说:"那位《科学前沿》的编辑,你们觉得他是真的对理论感兴趣,还是只想找个题材做嘲讽报道?"
"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林小雨说,"这都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你理论的机会。关键是你如何把握这个机会。"
李默握紧茶杯,感受着手心的温度:"没错,这次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无论被多少人嘲笑或批评,只要理论是正确的,就值得为之奋斗。"
窗外,新加坡的夜空繁星点点,仿佛在向他诉说着宇宙的奥秘。李默知道,他的学术之路才刚刚开始,前方还有更多挑战等待着他。但今天的挫折也让他明白,他不是孤军奋战——有林小雨的哲学智慧,有陈教授的科学指导,还有那些尽管不多但依然保持开放心态的研究者。
灾难性的演讲已成过去,但量子信息场理论的征程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