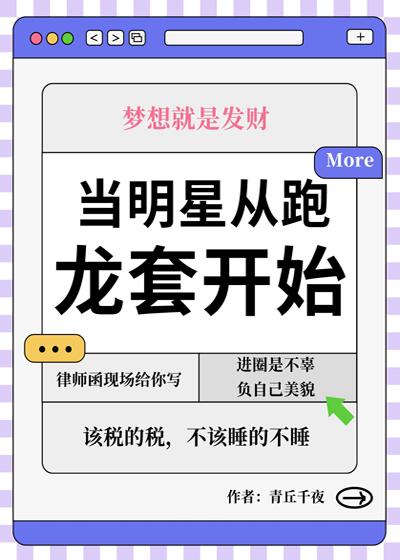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权倾朝野在线阅读 > 第13章 内阁更迭(第1页)
第13章 内阁更迭(第1页)
长春宫的暖阁里飘着龙涎香,苏若雪望着太后鬓间的东珠簪子,忽然想起淑妃手记里画过的同款纹样。自顾承轩的密信提到“崔尚宫”,她已三次求见太后,今日终于得了召见,袖中藏着的,正是从崔尚宫梳妆匣里起获的赤金耳环——与淑妃画像上的饰物分毫不差。
“明珠来得正好,哀家这几日总梦见你娘。”太后靠在金丝楠木榻上,语气慈祥,却在看到苏若雪手中的锦盒时,指尖轻轻一颤。盒中耳环在烛光下泛着冷光,崔尚宫昨日暴毙前,曾对着这耳环磕头如捣蒜:“是皇后娘娘让奴婢换的安胎药……”
“太后可还记得,二十年前淑妃娘娘薨逝时,崔尚宫是您身边的一等女官。”苏若雪跪在蒲团上,声音平稳如镜,“赤焰卫在她房里搜到的账本,记录着顾延之每年往长春宫送的黄金数目。”她顿了顿,取出一卷羊皮纸,“还有燕王去年冬日的拜帖,上面写着‘请太后为北疆军务美言’。”
太后的脸色骤然变冷,东珠簪子在鬓边摇晃:“哀家不过收些孝敬,难不成你要学顾延之,诬陷哀家谋反?”苏若雪叩首在地,却不退缩:“不敢。只是崔尚宫已死,淑妃之案再无对证,还请太后准许本宫将长春宫的旧人调去刑部问话。”
殿外突然传来通报:“礼部林大人求见长公主殿下。”林墨白的声音带着风雪寒气,他刚从秋审现场赶来,官服上还沾着刑部的朱笔印。苏若雪起身时,注意到太后的目光在林墨白腰间的赤焰卫令牌上停留——那是皇帝昨日刚赐的,可调动五百禁卫军。
“江南八百里加急。”林墨白将血书递到苏若雪手中,素白宣纸上染着暗红指印:“新科进士张元在苏州遭伏击,临死前指认吏部尚书吴明远私扣赋税银三十万两。”他转向太后,恭敬行礼,“此事涉及国公府旧部,臣恳请太后准许彻查。”
太后盯着血书,忽然冷笑:“吴明远是你公公,苏若璃的公公,你就这么不顾情面?”苏若雪心中一凛,太后这是在挑明她与国公府的恩怨。她正要开口,林墨白已抢先道:“律法面前,岂容私情?何况血书上的指印,正是吴明远的管家所留。”
长春宫的气氛剑拔弩张,苏若雪忽然瞥见太后袖口露出的半幅蜀锦——与顾延之书房里的屏风纹样相同。她突然明白,太后与顾党早已勾结,所谓“收孝敬”不过是表象,真正的目的是借江南士族的银钱,支持燕王谋反。
“既然如此,哀家就准了。”太后忽然换上笑脸,“不过明珠啊,你如今是长公主,可别被寒门书生迷了眼——”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林墨白一眼,“当年淑妃就是太信男人,才落得个暴毙的下场。”
离开长春宫时,暮色已合。林墨白望着宫墙上的积雪,低声道:“赤焰卫在吴明远的库房里,发现了印有燕王徽记的兵器。”苏若雪点头,想起方才在崔尚宫房里看到的玉佩,正是燕王独子的随身之物:“太后想借吴明远的手,把水搅浑,让我们顾此失彼。”
两人在紫禁城的长街上走着,宫灯将影子拉得老长。路过内阁议事厅时,忽闻里面传来争吵声:“长公主干政,成何体统!”“遗诏明言共议国政,尔等敢抗旨?”正是三朝老臣李太师的声音。林墨白轻笑:“看来,该是内阁更迭的时候了。”
次日早朝,金銮殿上气氛凝重。苏若雪身着赤焰纹礼服,与林墨白并肩而立,身后站着新提拔的监察御史张元——他的兄长张正,正是秋审中被平反的冤案当事人。当林墨白展开吴明远的贪墨账本,殿中重臣皆倒吸冷气。
“吏部尚书吴明远,私扣江南赋税,勾结藩王,证据确凿。”皇帝萧衍的声音带着怒意,“着即革职下狱,由礼部尚书林墨白暂署吏部事务。”此言一出,顾党的核心成员纷纷变色,右相王承恩刚要抗辩,苏若雪已取出崔尚宫的账本:“右相大人去年收的二十箱西域香料,可还记得是从哪儿来的?”
王承恩的脸色青白交加,忽然跪倒在地:“臣、臣愿辞官归隐……”未等他说完,殿外突然传来骚动,国公府嫡女苏若璃闯入殿中,手中捧着鎏金匣:“陛下!臣妾有国公府遗书,请为亡父做主!”
匣中羊皮纸展开,赫然是国公爷的绝笔:“顾延之勾结皇后,毒杀淑妃,皆因老臣力保长公主……”苏若雪瞳孔骤缩,这字迹与淑妃手记上的不同,却盖着国公府的朱砂印。她忽然想起,国公爷临终前,苏若璃曾贴身照顾三日——定是那时伪造了遗书,意图将水搅浑。
“好巧,本宫也有一样东西。”苏若雪从袖中取出赤焰卫截获的密信,“燕王写给顾承轩的信,说‘待内阁换血,即可清君侧’。”她扫过苏若璃,“堂姐莫非不知,伪造遗书,按律当斩?”
苏若璃的脸色瞬间惨白,手中的羊皮纸飘落,恰好盖住吴明远账本上的“苏府”二字。她忽然尖叫:“你不过是个养女,凭什么骑在我头上?当年若不是我娘把你从乱葬岗捡回来——”
“住口!”皇帝拍案而起,“国公府护驾有功,朕念着旧情,饶你一命。即日起,禁足苏府,再敢出府半步,斩!”苏若璃被拖走时,怨恨的目光像淬了毒的刀,却让苏若雪更加确信:顾党余孽未除,藩王蠢蠢欲动,这内阁,必须彻底清洗。
退朝后,内阁议事厅换上了新的匾额。林墨白看着眼前的六位新阁臣,其中三位是新科寒门进士,两位是北疆提拔的将领,唯有李太师留任,却主动交出了票拟权。“接下来,该整顿六部了。”他对苏若雪低声道,“尤其是户部,吴明远的人还在暗箱操作。”
苏若雪点头,望着议事厅外的雪景,忽然想起在冷宫的那个夜晚,陈嬷嬷说的“遗诏分两半,合则天下安”。如今她与林墨白,一个掌赤焰卫,一个署吏部事,正应了遗诏中的“共议国政”。而方才在殿上,当皇帝将首辅的玉笏递给林墨白时,她知道,真正的内阁更迭,才刚刚开始。
“对了,”林墨白忽然取出个紫檀盒,“这是从吴明远书房找到的,你看看。”盒中躺着半块蟠龙纹印泥,与顾延之私藏的那半块严丝合缝——正是当年伪造太子密信的证物。苏若雪轻笑,将印泥收入袖中:“明日让御史台弹劾王承恩时,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暮色中的紫禁城飘起细雪,长公主府的灯笼次第亮起。苏若雪站在廊下,看着林墨白在雪地上踱步,手中握着新拟的阁臣名单。他的青衫上落满雪花,却衬得眉目愈发清朗,正如他们初见时,那个在洞房中掀她盖头的寒门书生,如今已成为能与她并肩的内阁首辅。
“墨白,”她忽然唤他,“你说,太后会就此罢休吗?”林墨白转身,眼中是成竹在胸的笑意:“她若敢动,我们便借燕王的弩箭案,连她的亲卫一起端了。”他顿了顿,声音轻下来,“何况,我们还有赤焰卫,还有天下寒门士子。”
雪片落在赤焰纹的灯笼上,腾起细微的热气。苏若雪忽然明白,所谓内阁更迭,从来不是换几块匾额、罢几个老臣,而是要在这盘根错节的旧体制中,种下新的种子。而她与林墨白,正是这新体制的奠基人,用遗诏的权威,用寒门的力量,用赤焰卫的刀锋,为昭华朝劈开一条新路。
远处传来更鼓,已是戌初时分。苏若雪看着林墨白在名单上圈下“张元”的名字,忽然想起他在秋审时说的话:“律法如刀,不斩蝼蚁,只断权臣。”如今这把刀,终于握在了他们手中,而内阁议事厅的新匾额,在风雪中愈发锃亮,仿佛在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那个先帝遗诏中,长公主与首辅共理的太平盛世,正在缓缓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