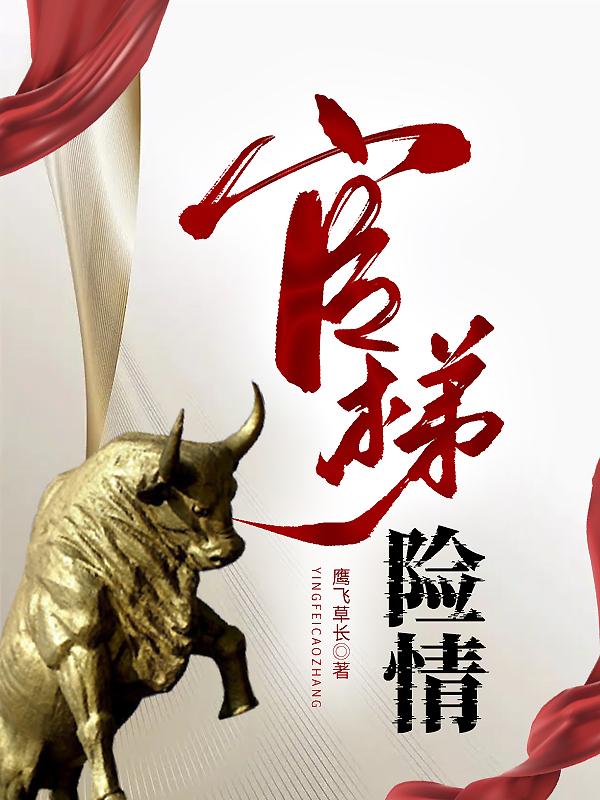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替嫁之将长佩 > 第95章(第1页)
第95章(第1页)
楚翊恍然,连敲自己脑壳:“蒙冤之人都想洗刷冤屈,我被这个思路困住了。没错,该反其道而行之!”
他从雪堆起身,振了振棉袍的衣摆,看向罗雨,“把府里会写字的都召集起来,要开始反击了。”
若说每日生活是一场试炼,那起床便是头一关。天冷时,这关格外的难。
人们骂骂咧咧,不情不愿地爬出被窝。吃罢起床更早的老婆备好的饭食,然后出门谋生,却被夹在门缝的纸张驱散睡意。
冷风掠过一列列工整清晰的小楷,似乎是宁王在江南开销账目的完整版。
这是当前世面上探讨最多的话题,比那些娘们儿偷汉,婆媳大战的烂事更引人注目。走到哪,都有人在说。那些家伙不厌其烦,简直像收了钱在故意散播。
天子脚下,首善之地,民众都多少识几个字。目不识丁者,也很快在各类酒肆茶馆得知了账目全貌。除了已知的,还有更离谱的:
驸马,即宁亲王,每日都吃生虎鞭蘸辣椒,早晚各一根;
五斤以上的人参,蘸大酱啃,早晚各一根;
一种名为“象”的南国大兽,每头两千多斤,骑在背上抱着啃;
夜宵吃手擀面,必须是十丈长的一整根,中间不能断,酱冰块、卤雪花做浇头;
为彰显德行,每顿饭都要求当地十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自愿作陪,饭后还要与这些花甲重开的老人载歌载舞,比掰手腕,切磋拳脚……
第170章跑这么快,想我了?
人们纵然循规蹈矩,天性却总是爱追逐离奇。因降雪骤冷的天气,加快了离奇韵事的传播。大家都爱喝一碗热酒,一盏热茶,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
再愚笨的人,也品得出其中的诡异。
“七两为参,八两为宝,普天之下哪有五斤的人参?又不是大白萝卜。”热闹的酒馆里,一人眯缝着眼,咂着烧酒说道。
“就算十丈长的手擀面勉强能做,那酱冰块、卤雪花怎么做?太可笑了。”另一人也附和。
“人活七十古来稀,满世界难找一百二十岁高龄的老者,江南单单建同府就有十个?还载歌载舞,掰手腕?”说话的男人撇嘴摇头,表示不信,“太明显了,整件事压根儿就是假的,有人故意编排诋毁宁亲王呢。”
“不,这里面有真有假,不能因为那些离谱,而忽略了真实啊!”庆王府的家丁混迹其中,试图纠偏。然而,公众的兴趣苍黄翻覆,人力与金钱只能顺水推舟,却难以调转方向。
“那么,该如何分辨真假?愿闻高见。”角落飘出一道清朗的声音,是个独酌的布衣少年。嘈杂沉寂了一瞬,客人们怔愣着,一时竟忘了呼吸。
少年英气绝美如谪仙,一对清凌凌的黑瞳,闪着无畏无邪。分明身处乌烟瘴气,周身却似有烟霞轻笼。叫人不由得担心,酒馆油腻的桌面,会玷污了那随意搭在上头的手。
“这……”庆王府的人被问住了,磕磕巴巴道,“宁王都被参了,那……那参他时列举出的账目,肯定是真的,里头没什么吃大象这些。后来传出的,分明就是有人在混淆视听。”
“哦?莫非你是官府的?”少年慢条斯理地斟一杯酒,“那你带大家去看看,参他的折子怎么写的,都在通政司存着呢。”
“对啊,带我们去看看吧!”众人起哄道。
那岂是随便看的,庆王府的人讪讪不语,又叫了一壶酒。这时,酒馆门前来了走街串巷的说书人,步履悠哉,半唱半念地叨叨:
“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这人头发斑白,脊背微驼,留一撮山羊胡。有人爱听,给几个铜钱,他便支起鼓架,定好弦音,舌灿莲花地讲上一个时辰,腹中有成千上万的故事笑话。
说书人踱进酒馆,抑扬顿挫地念了一段俏皮话:“王公贵族吃大象,还要人参蘸大酱。酱冰块、卤雪花?真是离谱把门敲,嘿,离谱到了家。”
这话成功逗笑了所有人。尽管没人掏钱买故事,说书人还是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城里某贵胄,如何骑在大象背上生啃。越讲越离奇,完全脱离真实。
“这位爷后面还骑着个小美人儿,你们猜是干嘛的?”说书人煞有介事地压低声音,酒馆里的客人都紧盯他的嘴,“负责剥蒜的,啃大象得就着蒜才香!”
一阵哄堂大笑。
“道听途说而已,真假诸位自行判断。”讲完一段,说书人整整褡裢,出了酒馆,又奔另一间茶坊而去。
天色渐晚,叶星辞喝光面前的酒,抹抹嘴角,结账离开,与伙伴们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