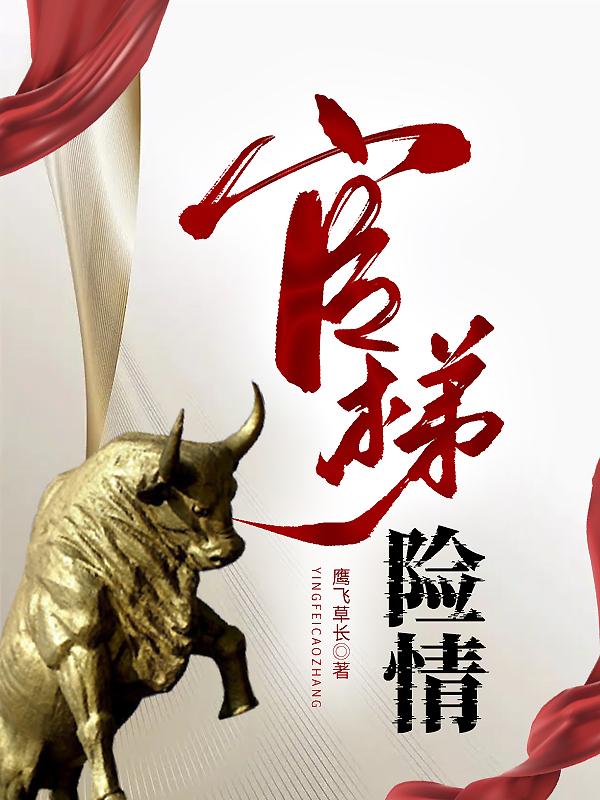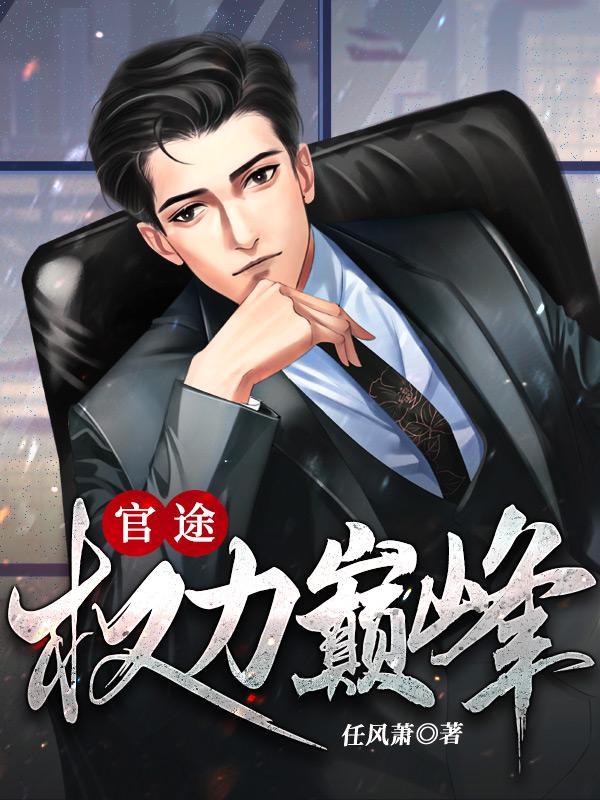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折青欢最新章节更新内容 > 第 14 章(第2页)
第 14 章(第2页)
她怎么就忘了萧秋折尚有一祖母在堂。
亲王府到萧秋折这一代,尚未有子嗣降生,而萧秋折身为嫡长子,此重任自是要落在他们肩上。
玉儿见她眉宇间愁云满布,却自个儿笑得眉眼弯弯,心想若是这对别扭夫妻能因此生情,倒也是桩美事。
遂婉言劝道:“小姐自幼长于京城,岂不知京城男儿郎何等模样?且不论相貌,但凡有些家世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甚或在外拈花惹草的,风流成性的。像如姑爷这般品性端正的,实属凤毛麟角,京城之中,恐难寻得其二。”
玉儿近来经常夸赞萧秋折,令晚青妤颇感无奈。她以帕拭面,移步门外,扯了扯唇角:“你日后少说这些,若无两情相悦,再好亦是枉然。”
玉儿紧随其后,见她眉间微蹙,不敢再多言,却正撞上方于直勾勾的目光。玉儿眨了眨眼,这才想起来门口还站着一个通风报信的。
估计今日这事很快就会传到萧秋折耳朵里。
方于见她眨眼,眼皮一跳,耳根瞬间红了。
玉儿瞧他呆愣,说了一句:“别啥都告诉你家公子。”
然后追上晚青妤,问道:“小姐要去哪里?”
晚青妤:“去探望外祖母,上次回京未得相见,她身子一向欠安,自外祖父去世后,便独居老院,我过去看看她。”
晚青妤十岁前皆是在外祖母膝下承欢,彼时外祖母对她疼爱有加,常为她烹制蜜糖酥,又常为她讲述神话故事,她对这些故事好奇不已,每每听罢皆会执笔记录。
彼时,付钰书的家恰在外祖母家隔壁,两家相邻,往来频繁,她亦是在那时与付钰书相识。
而后,她与付钰书渐熟,便开始一同聆听外祖母讲述故事,又一同执笔记录。
那时,付钰书写下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并且赠予了她。
再往后,他所著文章在京中一鸣惊人,后小有名气,年纪轻轻就在文学方面拔得头筹。
晚青妤看过付钰书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皆不止一遍,她能从其文字中窥见,他是个极具个人魅力之人,不喜束缚,满腔热血,心怀拯救苍生之志,却又隐隐透露出对命运之不满。
方于见主仆二人欲出门,急忙跟上,又唤管家备车。
晚青妤的外祖母仍居乔家老院,距城门不远,亦近付家书库。晚青妤顺路采买些礼品,三人遂至乔家老院。
晚青妤望着熟悉的宅院,忆起儿时点滴,亦想起父亲曾背着她在院中枣树下摘枣。如今枣树依旧,然而父亲与大哥已不在人世。
乔家老院广阔,处处皆是岁月痕迹,院中仅住着外祖母及几名仆从,显得格外冷清。晚青妤心中感慨万千,缓步向内行去。
府上管事的张伯伯见晚青妤翩然而至,不禁面露惊喜之色,连忙上前拱手道:“三小姐。”
张伯伯随侍外祖母多年,如今虽年事已高,仍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实在令人感佩。他早年丧妻,膝下仅有一子,名唤张攸年,年方二十。张伯伯含辛茹苦,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幸得此子勤奋好学,才华横溢,颇具风骨。
一年前,张攸年得晚青禾赏识,调入言书堂当值,张伯伯感激涕零,誓言竭尽全力照料外祖母以报恩德。
“张伯伯。”晚青妤含笑唤道,语气温婉,“祖母近日可安好?”
张伯伯引她入内,笑回道:“老夫人一切安好,只是时常挂念三小姐。早知三小姐回京,老夫定当登门拜访。”
晚青妤莞尔一笑:“我回京不过是寻常之事,张伯伯不必如此客气。攸年哥哥近来可忙?”
提及张攸年,张伯伯神色微变,随即笑道:“年儿许久未归,想必公务繁忙。”
晚青妤目光微凝,试探道:“张伯伯可曾听闻言书堂之事?”
张伯伯脚步一顿,惊道:“言书堂出了何事?莫非年儿给青禾惹了麻烦?”
晚青妤轻笑安抚他:“张伯伯莫急,言书堂近来事务繁多,攸年哥哥未能归家,想必是因公务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