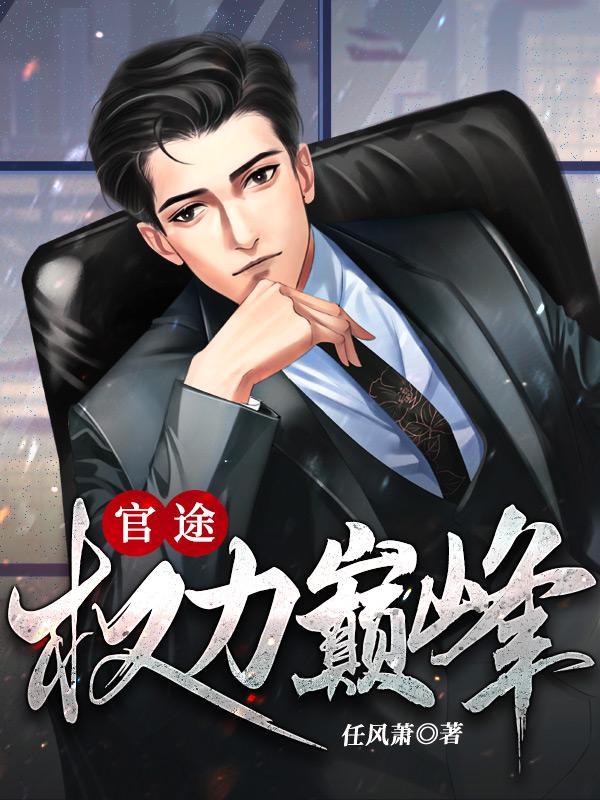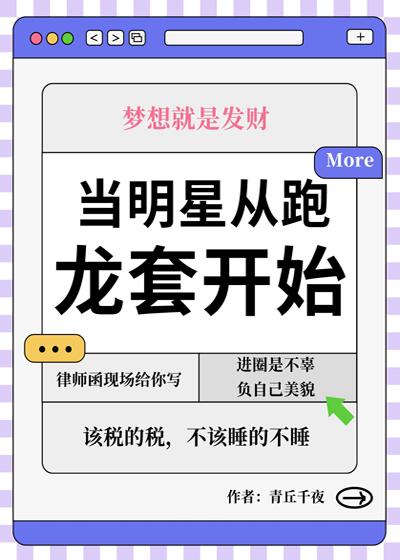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真少爷和假少爷在一起的 > 2530(第14页)
2530(第14页)
可今日忽然贬礼部尚书,东华书院出身的礼部尚书,又强势调镇国公来当礼部尚书,还当庭对礼部做了新的解释。这一举动的的确确再打东华书院的颜面。
晚上又来这么一出大戏……
让他内心就忍不住蠢蠢欲动。
被注目的阁老们自然也听出苏从斌话语中的坑,但谁也没有率先有所行动。反而都颇为从容,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看向还在滔滔不绝解释的苏从斌。
“第五礼亲。这一点开始格外重要,将孝正式纳入了政治范畴。”苏从斌刻意咬重了音调,希冀远在旁听席的亲儿子一定一定一定要听进耳朵里。
他和苏琮互相打配合,或许这回还能全身而退,甚至谋取些好处。
哪怕谋不了任何好处,小命肯定还会在。
毕竟苏琮对安乐侯的救命之恩!
毕竟他苏从斌昔年帮过大姨妈,定国公和太后捏着鼻子都得捞他小命。
否则皇帝黑历史抖出来了。
尿裤子的那种!
想着,苏从斌甚至还飞快横扫了眼旁听的方向:“《论语·为政》中孔子回答“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家孝敬父母团结兄弟,就是在朝左邻右舍做表率,就能带动一村的行为举止。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从政,就是在为国做出一些贡献。”
敏感察觉到亲爹望过来的和善小眼神,苏敬仪恨不得立刻点头若小鸡啄米,恨不得冲人身边喊一句放心我不傻。他为自己小命着想都不会贸贸然开口。
只不过罗列出一二三四那么多要求,等会苏琮该怎么辩啊?
继续用太、祖爷吗?
皇帝为什么要问苏琮本身的态度啊啊啊啊啊?!
苏敬仪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而苏琮见苏从斌这眼神的变化,眉头一挑,带着些了然。敬仪先前就强调过谏亲这一点,应该就是父亲耳提面命诉说孝道的无奈了。
可……可敬仪说得也对,任何事物都有兴衰发展的过程。
儒家也有衰落的时候。
甚至孔家子弟,还有南孔北孔的内乱呢。
所以大不了宁为玉碎,用商户苏家的九族换儒家衰败!
苏琮想着,眼角染上一丝疯狂的阴鸷。但这一抹阴狠消失的极快,他又乖顺的垂着头,静静的听得苏从斌的介绍。
苏从斌字正腔圆:“第六谏亲。有道是小仗则受,大仗则跑。便是要孔夫子教导子女要学会区分,学会不要盲从父母。”
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以指责父母不慈不顺从父母的一条孝道,苏从斌语速依旧:“第七光亲。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简言之做建功立业,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莫要因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
“第八,延亲。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需要生儿育女,延续香火。”
“以上八亲。便是微臣能够想到有关儒家对孝的定义。”苏从斌说完,朝帝王叩首。
武帝神色淡淡嗯了一声,除非亲近之人,完全让人无法辨认喜怒。而作为帝王的姐夫,镇国公表示他分辨出来自家皇帝小舅子的不喜了。于是他清清嗓子,开口:“皇上,臣出身也不是什么秘闻,臣就是天生神力会打仗。真没读过几本书。所以对这叨叨叨的一串,微臣不理解。故而微臣作为礼部尚书,没法把这话复述给帝王听。甚至末将还厚颜,您要不问问其他朝臣对孝的规定吧?尤其是科举出生的朝臣。”
说完,镇国公似想起什么,飞快纠正:“不,是文科出生的朝臣意见。这种叨叨叨的,跟我们武将,跟我们武举不搭嘎的。”
他就是如此鲜明仗义的,直接一张口就见所有武将全都包圆了,远离这种打嘴仗的破事。
在朝的武将们对此都颇为感动,互相隐晦的动了动象牙笏板。表示有数——聚精会神做好打架准备!
武帝瞧着态度明确的镇国公,倒是也一点没怒,反而笑着:“你这礼部尚书先前可踊跃的很,朕还以为你好歹也学了点知识。先前安安还道你这个当爹的要争口气,陪着他一起读书认字。”
真不是他宠外甥,而是不好学这传承亲爹的。
“皇上,末将知道吴下阿蒙这个词的。而且还知道东坡肉他爹二十七才开始读书。”镇国公含笑回应:“末将今年三十五,战功有了,也休息了两年。正好眼下是解甲归田,跟我妻儿一起效仿古人,边种田边读书,叫采菊花打南山踏平东黎山。”
朝臣们:“……”
武帝:“……”
武帝不太想跟莽夫姐夫拉家常了,直接睥睨在场文臣。
这一眼,意味深长的,震的本就思绪百转千回的文臣额头都溢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甚至各部都暗暗祈求别点名。毕竟一不留神或许就是神仙打架,殃及池鱼,就是多年奋斗化为虚无。
“苏琮,在一天之前,你是大周最年轻的秀才公!”武帝视线越过文臣,最后停留在跪地的苏琮身上:“朕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前秀才公,对你养父苏从斌,朕的礼部国子监祭司所言的孝,有何点评?”
“这礼部国子监祭司一职,可需要点真才实干,否则看起来都压不住不懂公审礼法的学生们!连最基本十岁不受刑的律法都不知道。”
听得帝王这声点评,前来的学生们,尤其几个先前仗着还未开审内涵苏家权贵内涵苏琮有通天关系的学生们面色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