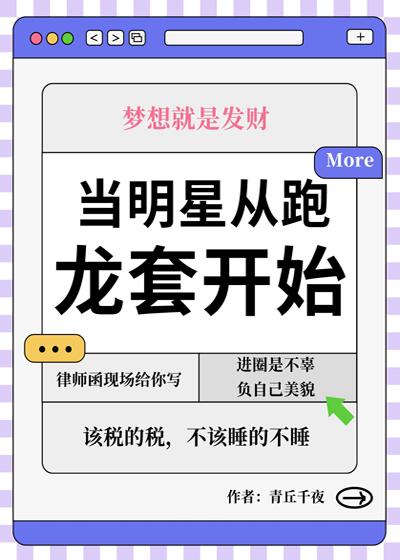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穿越成贾琏的推荐 > 第119章 海湖书院(第1页)
第119章 海湖书院(第1页)
作为北方极为有名、现在极为着名的书院,海湖书院创于天佑后期,创始人是颜学门徒,位于顺天府和易州边界上,临河而建,往北是房山,向东顺流而下可以到达涿县,但距离最近的城镇是向西处于易州境内的石亭。贾兰进入书院已经有近一年了,他比起在贾家时的生活变化极大。四月初四这天,天边的鱼肚白初露,贾兰就已起来,和同屋的同窗们,背起书袋,出门汇入人流,这是大家要去上书院的早课。海湖书院的早课是自习和阅读朝廷邸报,不过学子们比起经书,更关心朝政。心急的都是跑着去课堂的,等到贾兰和朋友刘泉迹、王渡进学堂的时候,放在教案上的十份抄报早被人给瓜分了,慢了一步的其他人只得聚在关系比较近、手里拿着抄报人身边,挤在一处看。于是贾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泾渭分明的一个又一个小群体,贾兰早就习以为常,同朋友们找了一处座位,从书袋中拿出一两本要温习的书,放到桌上。但是呢,不翻开来看,而是等人。“今天怎么了,圭介这么晚还没来?”嘴里嘟囔的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刘泉迹,其父是川中有名的大富商,平日里也是挥金如土的人,几次出书院到城里去,贾兰有幸看过。可惜书院内严禁攀奢,连学生们的衣服都是制式的。刘泉迹家中虽富,但身形不富态,反而娇小。王渡正准备接下他的话茬,看向门口的眼睛突然一亮,拿手拍了刘泉迹的肩膀,口里喊到,“圭介来了。”刘泉迹马上从趴在桌上的姿态,直起身子来。贾兰也闻声抬头看,一个身形矫健的瘦小伙快步走到三人面前,随便将书袋往贾兰前面的书桌上一放,坐下还不等人问,就脱口一句,“快拿水来,我可累坏了。”贾兰连忙将自己的水壶递给他,小伙不客气地大口饮水,连灌几大口,才将水壶还给贾兰,再从怀里掏出一份纸,故作姿态,轻笑道,“久等了吧?”“拿来吧你。”王渡毫不客气从他手中抢过纸来,连忙打开看,刘泉迹手撑在王渡书桌上,伸出大半身子凑到他旁边,伸长脖子看。贾兰倒不着急,而是问起小伙,“圭介,今日邸报上都讲了什么?”被三人唤做圭介的小伙全名吕圭介,是书院附近涿县的人,他出身寻常百姓人家,祖父两代都是从耕从战的军户,到了他这一代,他有点读书的天赋,在众兄弟中出众,祖父做主,一路从乡间私塾供到海湖书院。但吕家人口众多,吕圭介虽然不缺日常吃穿,但还是勤俭为上。书院内有不少供家境贫寒者补贴家用的活,抄邸报就是其中一项。每日京城夜禁结束,城门打开,邸报就会被以快马的形式送到书院,然后交由书院中打工的学子抄录。抄邸报是个苦活,起的要早、字迹要好、速度要快,能长期坚持下来的没多少。吕圭介听贾兰问起,便从容讲起邸报上的内容,“头等大事就是蓟辽军偏军从唐马寨向东攻克船城、烟狼寨,前锋逼近沙河堡,而大军主力继续北上。”看着邸报的刘王二人也以看完这一段,听吕圭介讲起,不等看完其余剩下的,就问吕圭介怎么看。他们二人如此问,是有缘故的。海湖书院秉承颜元“兵农合一,文武兼备”的理念,除儒家经典,兵学亦是有授,并且有考核。但儒生不入军伍,不得精义,自创院以来都是虚有其事。书院历任山主自然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可上无阙门,只得往下觅计,将目光放到地方的军户身上,凡其有读书之才,只要愿意来读,皆纳之。于是海湖书院内部就有一个特殊群体,要论他们在经书上有多大能耐,还要与天下来此的年轻士人比较一番,但在兵事上他们多是独占鳌头,军阵演练、骑射、步战多科前十都是他们的人。吕圭介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的步战一科多年来都是第一。所以谈到打仗,刘王自然是要找比自己懂的人问,贾兰也有好奇心,看吕圭介的理解。吕圭介自看到邸报的那一刻,心里就在不断想,他们不知枢密院和蓟辽总督府的谋划,可有些东西他们还是看得到的。“从大军行进的方向和事前的准备来看,应当是效仿太祖、天佑年间的故事,依托水师河道进行作战。”吕圭介慢慢吐出心内所思,“偏军从唐马寨向东展开兵锋,绕过鞍山驿,直取沙河堡,就是在切断辽阳州同前线鞍山一带的布防,这样鞍山一带的后金军不撤也得撤,对于后金军而言,龟缩固守辽阳州是最好的打算。不过”“不过什么?”刘泉迹见吕圭介稍有迟疑,急忙问。“辽阳州是后金南部第一大城,常年同海城方向的蓟辽军作战,战力强悍,根据师长们闲聊透的口风看,辽阳州至少有四万后金军,如果放任辽阳州的敌人退守城中,打攻城战,而不是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恐怕对我们不利。”吕圭介讲出他的担忧。,!“为何?”“如果大军主力采取顺河向北的方略,过了辽中,就到了开城、新民州。新民州是后金西部大城,地域特殊,往西南是锦州府,往西是漠南三部中的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它们三年前在蓟辽总督府的支持下,击溃喀尔喀部,占据了喀尔喀部的地盘,而新民州往北是科尔沁,东南是后金都城盛京,可以用四战之地来形容,形势复杂。如果蓟辽总督府的谋划是沿河攻占新民州,一是补给线太长,就算采用水师河道保障后勤,辽阳州到盛京一线需要布控的范围也大了些,二是从新民州进攻盛京,北面的科尔沁必然要防卫,而且后金北部的军队,也会从侧翼威胁大军,怎么看都比较冒险。”吕圭介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这坐着的四个人里面就他的重心是放到兵事上的,另外三个都是攻读经书的。他们也只是好奇,要是论,多关心战事,也就是图个话闻个趣,做个日后的谈资。倒是吕圭介的引起学堂内几个同样在兵事上有研究的人的兴趣,拉着吕圭介讨论起来,预测总督府下面会如何用兵。等早课结束,贾兰他们要去书院外找吃早饭的地方,吃完饭还要回来上正课,到了下午正课结束,贾兰会同三人去藏书阁,参与京畿修缮河道工程梳理,将他们过去一年在京畿地区四处奔波看到的记录下来,写成文稿,交由夫子们审编。比起理学的书院,经世学派下的几所书院在实践上的要求高的多,功课也不只有书本上的经义。不过在进藏书阁之前,贾兰受了一顿嘲讽。“哎呦喂,这不是贾大少爷吗?怎么也要来这藏书阁,苦研经典呀?”在藏书阁门口,一个俏面儒生遇上贾兰,嘴上发臭,他身后还有十余人。“你什么意思,方纪,想打架是吧?”王渡直接站出来替贾兰跟儒生讲理。“王渡,我们可是读书人,动手动脚岂不粗鲁,有失身份。”方纪当然不会和王渡这个农家子动手,他那副手糙的很,眼珠子一转,就曝出一个惊天大闻,“贾少爷,我方才可是真心。你亲姑姑昨日被陛下封为德妃,可见你们家是何等受宠,更不用说你堂哥,那位年纪轻轻就被升任正四品九边参议了,正四品的高官,我们就是苦读十年也不见得能中举列榜三甲不是,考中了进士,想坐到正四品的官职,不知又是多少年了,说不得年老白头,也就是个知县。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方纪的话在藏书阁门口引爆学子们的话题,就是贾兰都在发呆,对于方纪说的他姑姑被封为德妃,他完全不知情,而且从来都没想过有这回事。不过他的不知情,不妨碍周围人对他的指指点点,毕竟双方家境不同,学子中绝大多数就能见见知县,要认识知府都是件难事,而贾兰这样的勋贵子弟就是皇室里的人都认识,姑姑被封为妃,还要来书院跟他们竞争,很难不让人非议。吕圭介和刘泉迹、王渡都有些意外,他们当然也知道贾兰是勋贵子弟,只不过平日相处着,完全看不出来,也没见他家人有多关心他,最多就是在贾兰那里吃过他母亲送来的糕点。昨日被封妃,今天书院里就有人知道了,可见有人的消息灵通的很。吕圭介观察了周围的情形,知道在这同方纪纠缠越久,越不利,便拉着贾兰快步走入藏书阁。书院有规定,藏书阁内不得喧哗,违者必究。刘王二人连忙跟上去,一路来到二楼。吕圭介特意找了个角落,避开闲人,按着贾兰坐下,低声劝道,“别理那些人的话,他们就是没本事,心里又妒忌,就你心乱,他们就高兴了。且坐着,我去拿书过来,咱们好写完稿,交上去。”刘泉迹和王渡,也找好位置坐下,小声劝说,叫贾兰不必心愁。贾兰腼腆地点点头,也拿出笔纸预备整理自己的文稿。吕圭介不多时就抱着一大摞书回来了,放到桌上,四人目标明确,同去看一本大部头——《江河水利工程考》。这是本朝水利工程的教科书,但这不是经世学派的研究成果,而是嘉祥十二年彭城侯在领导漕运衙门期间,大量吸纳西洋学说,同中国古代的相关典籍知识进行融合,由西洋教士和中国漕运、工部官吏一同编撰的。该书始成便名躁天下,但很快成为士人不愿去读的书籍,除非有志于水利工程,毕竟其中内容繁杂不说,还大量加入数理知识,比起经书来还要催人白发生。可惜经世学派将其纳入必读,海湖书院将其纳入必考科目,每年考核都有题目出自其中,使得书院学子对其爱恨交加,每年临近考试,都有人抱着它夜读哭泪。在四人捧书低头钻研时,海湖书院山主刘璧站在不易察觉处,看着他们。刘璧身后跟着两位夫子,藏书阁外的事自然不会逃出他们的关注,事实上刘璧在昨天深夜就收到消息了。“山主,可还是在想贾家的事?”其中一位年纪稍壮的,向刘璧探话。“陛下的心,我们看不透呀。贾家姑娘入宫都多少年了,也没见陛下有所关注,可是一朝花为凤,叫人困惑啊。”刘璧背手眼神明亮,语气悠悠。两位夫子对视,也都叹气,封贾家女为妃出乎所有人意料。:()穿越贾琏之慢节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