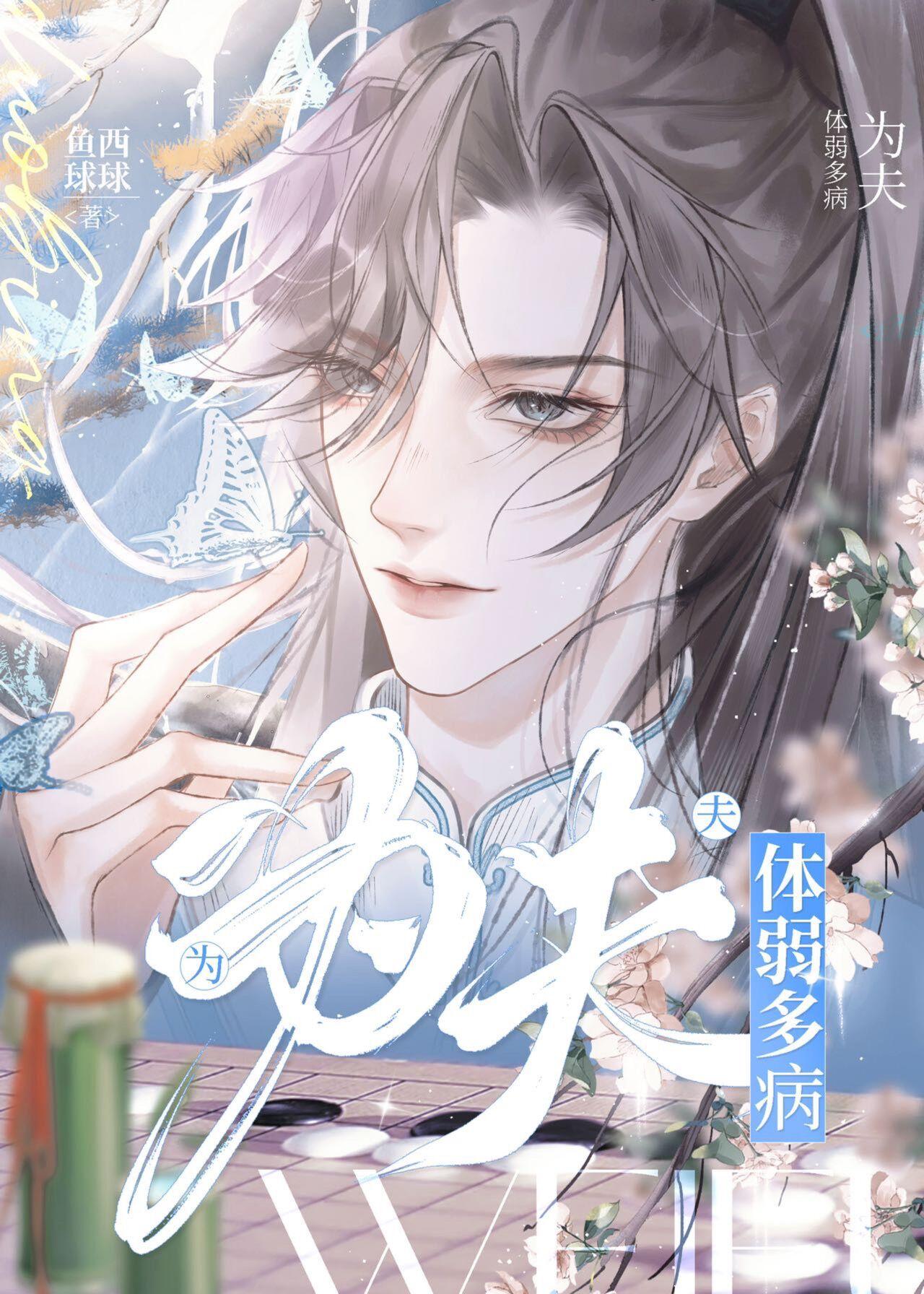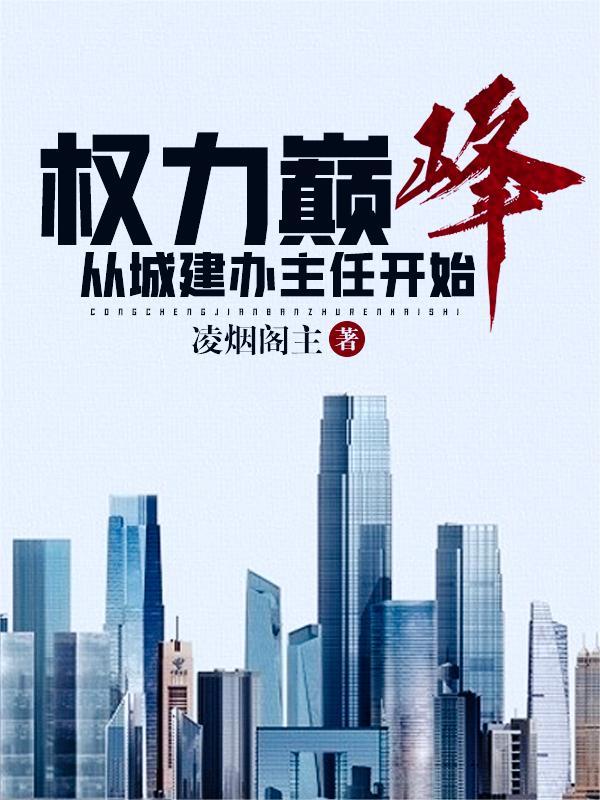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庶兄选了我前世的娘子 > 2第 2 章(第3页)
2第 2 章(第3页)
“我来便是。你先下去吧。”
卫嬷嬷上前,替主子按摩,边开了口,“您先前不是说,随二夫人去的。今日怎么过问起这事来了?”
二夫人送儿女回娘家的事,是来鹤柏堂说过的。老夫人那时并不是没觉出问题来,但沉默了会儿,最后还是点了头。事后她问起来,老夫人只是道,人都有私心,随她去吧。
可今日却当着众人的面,敲打了二夫人一番。二夫人险些面色都稳不住了。
江老夫人摇头,“余氏一门心思为三郎谋划,虽私心重了些,也勉强算慈母用心。她想瞒着,我也懒得掺和,只当遂了她的愿。但余家并非什么高门大户,能请来的,也不过尔尔罢了,就怕找些奇淫巧技、沽名钓誉之辈,耽误了孩子。况且,就算真是什么有才之士,半个月也获益匪浅了。”
卫嬷嬷听罢,只觉得自家主子良苦用心。
只是二房也好,四房也罢,各有各的私心。老夫人处事已经算是极公正的了,但各房私底下,怕是仍免不了抱怨。
卫嬷嬷不再提这些烦心事,转而说起了宜嘉来,“奴婢送参时,问了董家的。道是五小姐最近胃口渐好了,今早出门前,还吃了碗山药粥、两个素馅的小包子……夜里也睡得好,不大起夜……”
卫嬷嬷娓娓道来。
江老夫人听着,嘴上没说什么,眉头却是渐渐舒展开来。
--
宜嘉回了自己的院子。
过了中午,董妈妈去安排院里的杂事,留了大丫鬟宝音在屋里守宜嘉。
大雪的天,屋里静悄悄的。宜嘉从鹤柏堂搬出来后,便住进了绿漪堂。只有她一个主子的缘故,难免有几分冷清。但宜嘉倒已经很习惯了,也不用人哄着。因打算明日便销了病假,去进学了,便翻出书来,安静地在罗汉榻上看。
宝音在一边做绣活,见她看得久了,便柔声劝道,“姐儿看了这么久,歇一歇眼吧。”
宜嘉一贯听劝,闻言应下,放下书,朝窗外看。雪还未化完,望过去仍是一片的白,万籁寂静,这样冷的天,连鸟儿也不爱出门了,只零星几只掠过。
宜嘉看了会儿,回头问丫鬟,“宝音,是不是快要过年了?”
宝音掐着手指算了算日子,道,“再过五十来日,便要过年了。您怎的问起这来了?”
宜嘉摇摇头,没说什么。
离过年不到两个月,也没消息传出来。父亲今年大概也是不回的。对于这个答案,宜嘉也只是有些失落,类似一年的期待又落空了的情绪。但谈不上很难过。毕竟,从她记事起,父亲便不在身边,是一个模糊而不真切的存在。
看宜嘉不再问什么,宝音便放下手里的活,问道,“上午老太太赏了盒上好的孩儿参。董妈妈一回来,便叫灶上斩了只土鸡,吊了参汤,道是补人的好东西。您现下歇着,奴婢叫人去灶房端一碗来您尝尝可好?”
宜嘉其实不饿。
她总是生病,吃多了浓黑的药汤,对什么参汤补药的,一贯是有些怕的。但这参是祖母特意赏的,一番慈爱之心。宜嘉抿了抿唇,便很懂事地道了好。
参汤很快端上来,宜嘉安静喝完。宝音收拾了碗具,正要开口叫那丫鬟送回灶房去,宜嘉却忽地叫住了宝音。
宝音回头,“您可还有别的吩咐?”
宜嘉点了点头,仰着脸道,“明日带去学堂的糕点,多准备一份。”
宝音一愣,还当宜嘉自己嘴馋呢,劝道,“糕点吃多了积食,到时饭便吃不下了。”
宜嘉摇头,“我不是自己吃,是送人的。”
宝音这才放心下来,安排了个丫鬟去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