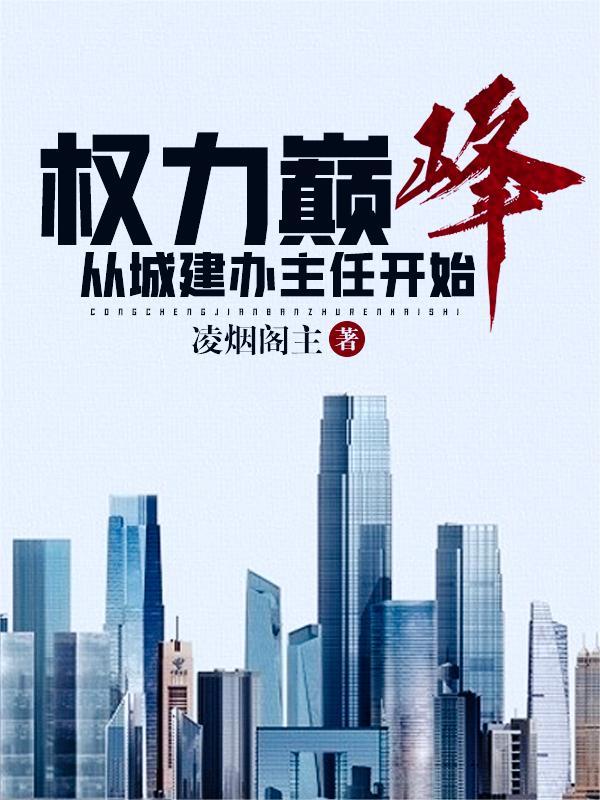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贵妃吐槽日常清穿宝音免费阅读 > 310320(第12页)
310320(第12页)
当然也幸好婆家是小门小户,不需要争那个贞节牌坊,才放她归家。
归家后她多是教育哥哥的孩子,才七岁的侄女可以说是她从小看到大。
眼下听哥哥这么一说,袁筝有些胆怯,“要不还是算了。”
多年未出门,出嫁前的手帕之交早已断了联系,袁筝习惯了闭门过日子,猛然让她出远门,去京城考女举,她不免退缩了。
袁机却鼓励她,“免除路费,去试试又有什么关系,正好我打算带江哥儿走一趟。”
袁机的长子袁江,早年调皮掉进过水里,之后留下了咳症,一到换季就咳嗽,杭州的大夫只说多养养,他听闻京城开了一家非常大的医馆,无病不治,便动了带儿子去治病的心思。
袁筝一听事关侄子的健康,便很快同意了,再说有哥哥陪着,去哪里她都不怕。
四月里,江南气候温润,不冷不热非常舒适。
袁家忙活起来,袁机的妻子夜里帮着蒸了一打梅干菜饼,这饼没有放荤油,冷了也能吃。
知道亲爹要出门,袁家小女儿吵吵闹闹也要去。
没人同意,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半大孩子出远门已经很艰难,再说路途遥远,小的路上生病可怎么办?
天蒙蒙亮,袁家兄妹便起床了,吃了点东西垫垫肚子。
袁机将长子叫起来,十岁的长子面色苍白,吸了一口冷气便忍不住咳嗽起来。
他立马捂嘴,怕把屋内的妹妹吵醒。
“爹……”
袁机推了推他,“快去洗漱,马上要出发了。”
门外传来动静,袁机去开门,就看到事先约好的黄包车到了。
近几年杭州城内多了不少黄包车,有人拉,也有前面安自行车的。
袁机妻子递过来梅干菜饼,袁机接过递给了外面的车把式两个。
梅干菜里放了辣椒,一点点辣椒很开胃。
袁机见儿子洗漱好,就拉着他上车,后面的袁筝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灰扑扑的老棉布挡住了外人的窥探。
两大人一孩子上了车,车把式快速地将剩下的饼塞进嘴里,再过来将油布帘子拉下来挡住清早的风。
袁江被父亲和姑姑夹在了中间,然后掏出了母亲包在报纸里塞他怀里的饼。
他小口吃着,感受到黄包车的颠簸。
等到了岸口,袁机扶着妹妹和儿子下车,顺手结了车钱。
他们此次是打算坐船到苏州,再从苏州转船走大运河到南京,在南京做通往北京的火车。
路程不算太远,往年得提前一两个月出发,如今行程已经缩短到七日内。
火车的诞生就是奇迹。
码头有往苏州的船,这边做客船生意的都被收编了,只能通过码头的售票处售票,主要是方便收税,同时也规范了船资。
售票处灯火通明,开着的是电灯,宽阔的大厅坐着不少人,也躺着不少人,都是等船的。
这边的船上午一趟下午一趟。
袁机的船票是提前买好的,走了几排才找到了两个连着的空位,他推着妹妹和儿子坐,他自个儿拿着包袱。
包袱里除了妻子给摊的饼,还有几瓶清水。
瓶子是玻璃瓶子,很久前装着罐头,如今装了凉白开,出门在外不方便,能凑合就凑合。
大厅通往码头有两扇门,这会儿用铁栅栏拦着,栅栏边上悬挂着一个牌子,白底绿字写着入站口三字。
过了一会儿,有人举着一个木板站在栅栏内。
“杭州通往上海县的十三号船马上启程,票是十三号船五点十分启程的来这边排队。”
很快陆陆续续有人拖家带口过去排队,栅栏外喊号的人喊了有几声,然后就看着墙壁上的挂钟。
等钟指针走到五点整才开栅栏,也没有仔细看票,只要手中拿着票就可以过。
等队伍里的人走完,栅栏再次被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