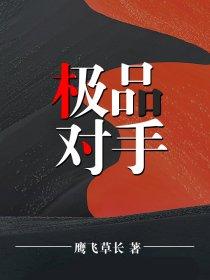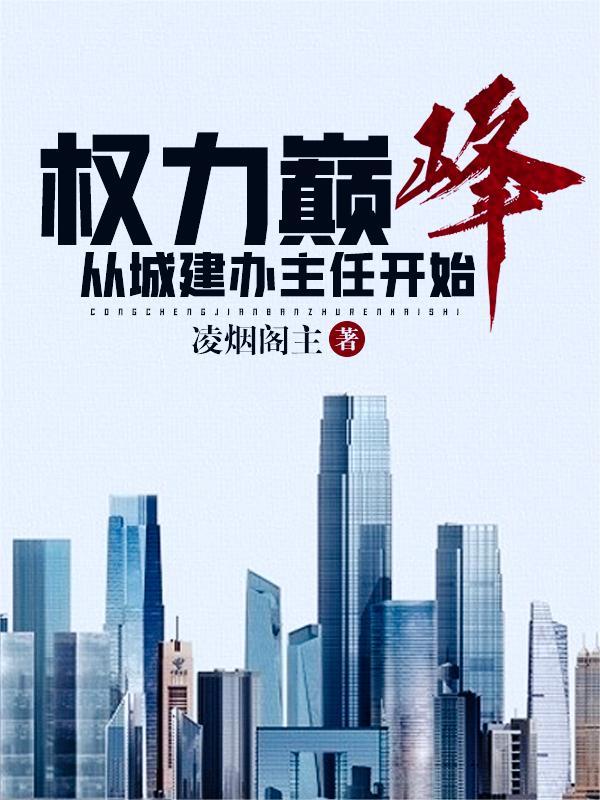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穿越做帝王的 > 第217章 修改荒唐的法律条文(第1页)
第217章 修改荒唐的法律条文(第1页)
回宫后,段智鸣直接来到了御书房里。他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思考着刚才在宫外审理的那起官司。虽然那件官司已经处理好了,但段智鸣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而已。那件官司是让自己撞上了,所以这个无耻的父亲才受到了惩罚,可其它没被自己撞上的呢?段智鸣觉得这种现象完全就是一种陋习,为了东宋的稳定和将来的发展,也为了公平公正,自己必须要把“不管父母对子女做了什么坏事,子女都必须无条件赡养父母”这条法律条文应该好好的改一改,消除这个陋习。于是,段智鸣思索了一阵后,就决定下旨,将“不管父母对子女做了什么坏事,子女都必须无条件赡养父母”这条法律条文修改成“父母要是对子女犯下了不能容忍的罪行,子女可不赡养父母”。正当段智鸣要下旨时,一个侍卫前来禀报,陈辉有要事在御书房觐见自己。段智鸣得知后,就暂停下旨,去御书房见陈辉。“陈爱卿有何事见朕?”来到御书房后,段智鸣直接了当的问道。“启禀皇上,有件案子,臣对其判决有异议,所以特来请求皇上主持公道。”陈辉回答道。“是什么案子,能够让你这个都察院的都御史亲自找朕来主持公道?”段智鸣听后,看着陈辉笑道。“回皇上,是一件杀人案,一个公公奸污了儿媳妇的妹妹,儿媳妇知道后,就到衙门状告公公,后来衙门以奸污罪判了公公死刑,但因为是儿媳妇状告公公,有违孝道,所以衙门还判了儿媳妇三十年徒刑。”“你说什么,儿媳妇到衙门状告公公的罪行,有违孝道,所以衙门判了儿媳妇三十年徒刑?”段智鸣不敢相信道。“是的,皇上。”“是你说错了,还是朕听错了,衙门怎么会做出这种荒唐的判决?”“皇上,微臣跟您一样,也认为这是很荒唐的判决,可很多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自古君王都是以,以仁孝治天下,宁可为孝而屈法。这子为父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这件案子中的儿媳妇知道公公犯了罪,却到衙门告发,这正是违背了子为父隐啊!还有就是,我朝律法也这是这么规定,亲属之间发现一方的亲属犯罪,不得揭发状告,否则将处以重刑。”什么狗屁逻辑?段智鸣心里暗骂,公公把儿媳妇的妹妹强奸了,儿媳妇将其告发那是有违孝道,违背律法,什么玩意嘛。段智鸣用现代的思维去思考东宋的规定,当然得出狗屁逻辑的结论。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并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此后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个原则,并加以发挥,唐朝扩大到了“同居相隐“,就是说没有亲属关系的奴婢等,也负有相互隐瞒犯罪的义务。明朝的法律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儿子包括儿媳,若向官府告发父亲、公公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儿媳处以重刑。当然,亲亲相隐原则的适用也是有其例外情况的。由于亲属相隐的理论基础在于“孝”,而根据儒家理论,封建社会的最高利益自然是臣民对君主的“忠”,那么,当忠和孝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舍孝而取忠。因此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也就是说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种罪,不适用同居相隐这个原则,必须揭发。陈辉说的话让段智鸣不敢相信:“你是说,我朝律法规定,亲属犯法,另一方的亲属倘若告发,就要被处以重刑,是吗?”“是的,皇上,微臣对这条律法非常的反对,所以才把这件事告诉皇上,请皇上下旨废除这条律法。”陈辉回答道。段智鸣没有想到,陈辉居然会和自己一样,非常的反对这条荒唐的法律条文,这让他感到一丝的欣慰:“你放心,朕立马下旨,赦免该案的儿媳妇,还有以前因为该条律法而入狱的人,同时朕也会废除这条律法。”段智鸣说完,就立马下了两道圣旨。一道圣旨是修改了“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的法律条文。另一道圣旨则是赦免了陈辉汇报的那件案子中的儿媳妇的罪,以及以前因为状告亲属犯罪而入狱的人,还把东宋的这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犯罪行为”的狗屁法律条文给废除了。两道圣旨下达后没多久,东宋境内几乎所有的人都闹了起来。他们一致要求,段智鸣必须收回圣旨,恢复“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和“允许亲属相互包庇各自的犯罪行为”这两条法律条文,并将那些释放的有违孝道的人全部都重新抓起来。,!尤其是朝堂上的官员,除了段智鸣的心腹外,其他官员在早朝的时候因为见段智鸣不同意收回圣旨,恢复“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和“允许亲属一方包庇亲属的犯罪行为”这两条法律条文,并将那些释放的有违孝道的人全部都重新抓起来,就全部在金銮殿跪下来请求段智鸣改变主意。面对东宋上下所有人的逼宫,段智鸣并没有任何的压力。他让朝堂上的那些官员全部都到宫外,自己则带着侍卫和禁军来到宫外,亲自跟这些官员还有那些反对自己废除“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和“允许亲属包庇一方亲属的犯罪行为”这两条法律条文的老百姓对话。“朕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朕收回圣旨?因为你们认为,仁孝可以治天下,宁可为孝而屈法”,可朕不这么认为,治理好天下,主要是靠律法,而不是仁孝,仁孝在治理天下中,虽然能起到作用,但起到的作用并不是主要作用,而是辅助作用,甚至于不但起不到作用,反而还会破坏国家的稳定;要是仁孝真能治理好天下,那你们告诉朕,为什么我们东宋的开国君王要在律法中规定,谋反、叛国这样的重罪大罪,亲属之间为什么不得隐瞒?”段智鸣说道。“天地君亲师,君在亲之前;既然君王要比长辈重要,那忠自然要比孝更为重要,所以在众多的罪行中,也只有谋反、叛国这样的罪行是例外的。”一个学者回答道。“说的不错,既然你们认为仁孝可以治天下,甚至比律法重要,那为什么我朝开国君王还要制定律法,不完全以仁孝来治国?”“回皇上,那是因为有些事情仁孝是解决不了的,还是需要律法处理。”大学士站出来说道。“好,既然是这样,那请你告诉朕,一个国家的稳定,是靠律法来维持,还是靠仁孝来维持?”此话一出,大学士只说了个“这”字后,就说不出话来。段智鸣见大学士说不出话来,就看向自己面前的民众问道:“你们大家也说说,一个国家的稳定,是靠律法来维持,还是靠仁孝来维持?”现场所有的人听到段智鸣说的这个问题后,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但就是没有人能够回答段智鸣刚才所说的问题。见现场的人都无法回答自己刚才提出的问题,段智鸣继续说道:“关于我朝规定亲属相互隐瞒各自犯罪”的律法,从明面上来看,是以仁孝治天下,可实际上还是以律法治天下,因为这条规定本身就是写在律法里的,所以这条规定就是律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真相;所以,维护国家稳定的是律法,而不是什么仁孝。”段智鸣说完后,现场所有人都点了点头。段智鸣见现场的人点了点头,知道他们都赞同自己刚才说的话,就继续趁热打铁道:“旧法规定,亲属犯法,除谋反、叛国外,其它罪行可相互隐瞒,既然是这样,那朕还要再问问你们,仁孝高于律法,是不是也意味着官员在执行律法的过程中,发现亲属犯了法,也可以隐瞒不报,徇私枉法?当然,你们可以说官员不包庇亲属,是因为官员在履行自己做为官员的职责,这是在尽忠;但你们要明白,尽忠不仅仅是官员的事情,也是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举报自己的亲属所犯的罪行同样也是在尽忠,毕竟不举报自己的亲属所犯的罪行,那么亲属随时会继续他们的罪行,给其他人,甚至是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你们说是不是?”段智鸣的这句话一说出来,现场所有的人顿时是心服口服。“皇上说的不错,的确是这么一回事,百姓举报自己的亲属犯罪,这是在尽忠,而不是不孝,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应该让皇上收回圣旨,恢复“允许亲属包庇一方亲属的犯罪行为”的律法了。”一个秀才说道。“没错,我也同意。”一个商人也跟着说道。“我也同意”……接着,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的跟着同意了起来。段智鸣见现场的人都同意自己说的话后,又继续说道:“朕再说说朕修改“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这条法律条文的原因,你们都认为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都必须要赡养父母,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这对子女公平吗?朕举个例子,官逼民反,老百姓为什么会造反,那都是贪官污吏给逼的,加上皇上是个昏君,不给老百姓做主;因此朕宁死不做昏君,在登位之时就全力反贪,当然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有一些贪污的官员,朕没有追究,这先不说;朕就说朕全力反贪的原因,朕全力反贪的原因就是为了不让老百姓因为贪官污吏的迫害而去造反,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镇压叛乱;同样,这子女就好比百姓,对子女犯下罪行的父母就是贪官污吏,如果朕不去修改“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这条律法,那结果就会是子女为了不赡养对自己犯下罪行的父母,而去弑父弑母,这可是有违孝道,比不赡养父母更是有违孝道,难道你们都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吗?”话落,段智鸣让侍卫把自己之前从刑部拿来的一些杀人案的案卷全部都发给现场所有的人查看:“你们好好看看这些案卷,这些案卷全部都是子女为了不赡养对自己犯下罪行的父母,而去弑父弑母的案子,看完之后再好好的想一想,朕废除“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这条律法到底对还是不对?”段智鸣这么一说一比喻,再加上段智鸣给的这些案卷,现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下来。段智鸣见现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下来,知道他们开始慢慢的同意自己修改的关于“不管父母对子女犯了什么罪行,子女都必须赡养父母”的法律条文了,也就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而是带着侍卫和禁军,一声不吭的离开了。离开的时候,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甚至是阻挠他离开。:()穿越世界做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