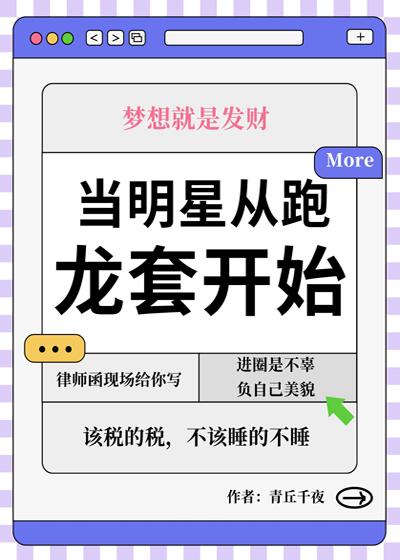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渣攻在强取豪夺文里重生后(不吃姜糖) > 6070(第30页)
6070(第30页)
崔帏之在营帐内纠结徘徊三日后,终于狠下心肠下令,梁军一拥而上,将匈奴军队尽数坑杀于雄马岭。
血混着夜晚的暴雨雷电淅淅沥沥下了一晚上,天晴之后,雄马岭地面的泥水淌着刺目暗红的血,崔帏之从顶上望下去,入眼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红。
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敌军的哀嚎和刀剑捅入血肉发出的声响,崔帏之看着下方一人叠着一人、不甘瞪着大眼睛仰望天空的尸体,再回头,看着身后将士们麻木又狼狈的脸,片刻后,终于红了眼眶。
四年青春尽皆化作热血和汗水抛洒在大漠孤烟和黄土枯骨之上,崔帏之率军出征时还未满二十五生辰,班师回朝之时,却已经年近三十而立。
这四年里,他黑了,瘦了,脖颈、后背、手臂和大腿上无一不新添疤痕;每每濒死昏迷之际,总是想到家中爱妻和三个爱子,只强忍着一口气,将家书放在枕下,希冀自己能够挺过去,看到第二天的日升。
江锡安在这四年里也被磨平了任何锋芒和性子。
本就因为毒损毁了根基,又在战场上吃尽风沙和苦头,军医告诉崔帏之,江锡安日后将终生无法离开汤药,且能不能活过四十岁,还得看天命。
逼退匈奴,班师回朝那天,崔帏之让人去清点了一下军队的人数,最后看着呈上案头上的数字,久久不语。
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二十五万的梁军将士,走的时候,只能带走剩下的五万人和剩下的二十万英魂。
一共死了二十万人。
一将功成万古枯,崔帏之回望这片土地时,每每回想到那二十万战友将士的面庞,还有尚且在家中殷殷期盼他们回来的家人,总不免被噩梦惊醒,后背冷汗铺湿了床单,再难入睡。
即便打了胜仗,可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行至皆疲惫沉闷不堪,处处一片愁云惨淡。
快要回到京城那天,崔帏之思念爱妻爱子,快马加鞭整整三日,不睡觉不梳洗,饿了就随便吃一点路边的吃食,渴了就装点泉水应付,跑死了足足四匹马,才回到京城。
进城门的那一刻,颇有些近乡情怯。
守城门的人还不知崔帏之回来了,看着面前这个衣裳破烂、灰头土脸,额前发丝因为没有打而随风飘散的陌生面孔,呵斥着让他下马接受检查,并出示通关文牒。
崔帏之只看了他一眼,并不答话。
在众人警惕地拿着武器靠近他,试图将他逼下马时,崔帏之才缓缓解下腰间的令牌。
一个“崔”字显露人前,令牌上面沾满了尘土、剑气和血迹,早就是一块伤痕累累的令牌,却让守城将士们瞬间大惊失色,纷纷跪下,齐声高呼“崔将军”。
城门缓缓打开,迎着众人崇敬又惊讶的神情,崔帏之归然不动地坐在马上,牵动马绳,往里缓缓走去。
看着街边的景色,熟悉又陌生,竟然有些恍惚。
京城早已不似往日繁华。
军队里一片愁云惨淡,皇城内便也是凄风苦雨,四年的战争,不仅是将士疲惫,百姓也颇为辛苦,连沿街的叫卖声都是有气无力的,举目四望,甚至一时都看不到一个穿着绫罗绸缎的达官显贵。
节衣缩食,尽供前线,大梁子民各个饿的脚步漂浮、面黄肌瘦,此刻能活着、能听到前线胜利的消息、不需要被屠城沦为奴隶便是大幸,哪有能力吃饱穿暖,甚至收拾自己?
看着满目疮痍,崔帏之竟然有些想要哭。
他仰起头,用掌心按去眼角的水液,随即凭着记忆,骑马走到崔府门前,在人们好奇的眼神里,缓缓下马。
一个四岁的孩童正扎着双髻,穿着最普通不过却又整洁干净的衣裳,专心致志地蹲在门口看蚂蚁搬家。
崔帏之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随即走到他身后,慢慢伸出手,迟疑几秒钟,还是轻轻将指尖搭在那孩童的肩膀上,轻轻晃了晃。
那孩童看见身后蔓延上来的大块人形阴影,下意识转过头,逆光看着一个浑身灰尘泥点、胡子拉碴、头发凌乱的大叔一言不发地站在自己身后,想了想,站起身,艰难地从腰带里抠出几个铜板,掌心向上,依依不舍地递给了崔帏之。
崔帏之:“”
他没有说话,只这样看着那灿金眸的孩童,动了动干涩皴裂的唇:“你”
“崔和真!你在干什么!”一个清脆的声音忽然从身侧响了起来,只听一声稚嫩的惊呼声,那孩童就被人抱了起来。
崔帏之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约莫十一岁的蓝衣少年将那双髻孩童抱了起来,后退几步,警惕地看着崔帏之,与崔帏之相似的眸子里全是惊恐和陌生:
“你是哪里来的要饭的?!要对我弟弟做什么?!”
崔帏之:“”
他上前一步,想要碰一碰崔降真的脸,崔降真登时扯开嗓子嚎了起来,抱着崔和真一路飞奔进了门,:
“母亲!母亲快来!有个要饭的要偷和弟弟!”
崔帏之:“”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站在原地兀自愣怔着,直到一个月末七八岁的小孩从门边探出头来,扒在门边,好奇地看着崔帏之。
崔帏之张了张嘴,哑声道:“颐真”
被叫到名字的小孩一怔,脸上浮现处些许狐疑,圆溜溜的灿金眸就这么一瞬不瞬地看着崔帏之,半晌,他才脆生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