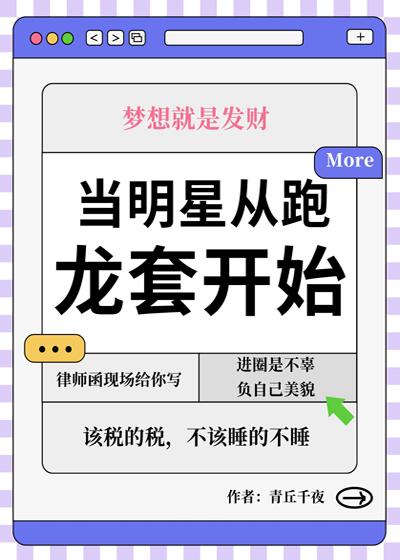乐狗小说网>红崖顶by洛奇 结局是he吗 > 第187章(第1页)
第187章(第1页)
沈思坐在晋王下首,只消一抬眼就能看到晋王的侧颜,透过那张喜怒无形、处变不惊的面容,他能很清楚地猜测到晋王在想些什么。毕竟他们都怀有同样的豪情夙志,都经历过同样的戎马少年。乘我大宛驹,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归根究底,这场战争因他而起,于公,他是晋王义子,本该身先士卒死而后已,于私,他是金葫芦的兄弟,兄弟有难,他理应刀山火海一往无前,更何况能与鞑靼人在战场上交手,对他而言也算乐事一件,在他心中有一团火焰,从不曾熄灭。
沈思轻轻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渐渐的,周围那些嘈杂的声音消失了,抱持着各种不同态度的人也都消失了。他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还是个总角小儿,被哥哥们带着站在烟尘滚滚的校场边看沈家军操练战阵,眼前是战旗被风翻卷得猎猎作响,耳畔是铠甲相互撞击发出锵锵之声。他依稀又听见了父亲在教导哥哥们:“凡战,以力久,以气胜,合军聚众,务在激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没错,两军阵前士兵能舍生忘死奋勇杀敌,靠的就是这股“士气”,设若“士气”没了,也就必败无疑了,此时晋军最最需要的,正是“士气”二字。
透过一片虚空,他问父亲:“阿爹,士气又从何而来?”
父亲循循善诱道:“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焚舟破釜,投之于险,置亡地然后存,陷死地而后生。”
是啊,该当要到焚舟破釜的时候了,且有些事非他不可。
再睁开眼睛,沈思已打定主意,他清了清喉咙,朗声说道:“诸位,沈思冒昧……”
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他,那些目光中有质疑有期许有敬服有抵触,当然还有一道饱含着深情与慈爱的目光,毫不掩饰落在他的脸上,热辣辣的,直暖到心里。
沈思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开口道:“行军打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瞻前顾后只会延误战机损毁士气,为今之计应该出其不意迅速发兵,一举击溃鞑靼人夺回葭州,如此不但可以鼓舞军心,还可震慑朝廷上下。”
话音未落,不知哪个小声嘀咕了一句:“说得轻巧,谈何容易……”
一向正直坦率的詹士台顺势说道:“末将对公子的想法深表赞同,但此举实在太过冒险,我军士卒数月来奔波征战疲累不堪,面对鞑靼精锐铁骑毫无优势可言,冒然应战若能成功便也罢了,万一失败,损兵折将暂且不说,还会引来鞑靼更加疯狂的反扑,到那时恐怕再想行缓兵之计,也不能够了。”
其余人纷纷附和:“正是,我等何尝不想痛快一战?然无必胜把握,谁敢担此重则?”
“我敢!”不待他人提出疑虑,沈思已先行下了重招,“我愿立军令状,白纸黑字,军法在上,沈思此去半月之内必夺回葭州,如若食言,提头来见!”
霎时间大帐内一片寂静,众人无不在偷偷窥视着晋王的神色,按说晋王该是要出言制止的,可等了好半天,晋王完全没有半点反应。
沈公子在晋王心里占多少分量,晋军上下尽皆看在眼里,沈公子的言辞便是王爷的言辞,沈公子的所为便是王爷的所为,沈公子的性命就是王爷的性命,如今沈思拿自己的人头立下军令状,无异于是晋王把自己的命压在了这一战上,君主尚且如此,身为臣子的,哪里还有畏缩不前的道理?
片刻之后,在座诸将纷纷起身拱手:“末将愿助沈公子一臂之力!末将愿听公子调遣!末将愿做先锋马前效力!”
沈思这才回头望向晋王,恰好晋王也在看他,四目相交,二人各自莞尔一笑,此时此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君高枕无忧,我便平安喜乐……只是这笑容背后,又蕴藏着万般艰涩,个中酸甜苦辣,不足与人言说……
议事直至凌晨方告一段落,来不及多加温存,沈思便点齐人马匆匆上路了。
出了解州,队伍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只用三天时间便赶到了汾阳府,稍事修正过后,又一路向永宁进发而去。沿途他们不断打探着葭州的消息,然而所获结果都与在解州听到的并无二致,所有人都知道鞑靼人杀来了,葭州失守了,可从始至终,没人见到过从葭州逃出来的一兵一卒。
沈思始终不愿相信葭州已全军覆灭,在他心里还留存着一丝侥幸,他记得他给金葫芦讲起过汉将赵破奴的故事。赵破奴是霍去病麾下的鹰击将军,曾在与匈奴左贤王一战中遭遇伏击惨败被俘,然而他并未因此羞愤自裁,而是花了三年时间,又成功从匈奴逃回了大汉。大丈夫者,能屈能伸,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他希望金葫芦记得这个故事,希望金葫芦也能像赵破奴一样,拼尽全力去保存自己的性命。
夜间队伍行至临县境内,前方开路的军士忽然来报,说途中遇到一名少年,自称是葭州守军,想要求见沈公子。身侧卫兵疑心有诈,正欲出言相阻,被沈思一摆手制止了。
很快,一名少年被带到了沈思马前,看模样只有十五六岁,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糊满污垢血迹,脏兮兮辨不本来面目,少年身后还背着个硕大无比的行囊,看去沉甸甸的,坠得他一直佝偻着脊背。少年见了沈思,“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怯怯问道:“敢问……您就是沈思沈公子吧?”说完不待沈思回答,他已重重磕了一个响头,“在下葭州守军刘小狗,拜见公子。”